24 疯狂的边缘
邦德一直期待着他熟悉的那个爸爸能醒来。他以为,只要我四处看看,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就能恢复成他所熟悉的那个父亲的角色。
但他很快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韦德曾提醒邦德要对两件事做好心理准备。第一,他不要指望我会记得刚从昏迷中醒来时所说的那些话。他解释说,因为记忆会占去大量的大脑功能,而我的大脑还没有恢复到能处理复杂信息的地步。第二,对于我醒来初期说的那些话不必太在意,因为我说的很多东西或许听起来会非常疯狂。
我接下来的表现证明了他的说法。
我醒来的第一个清晨,邦德非常自豪地把他和厄本画的画拿给我看。画面里是我的白细胞与细菌作斗争的场面。
“哇哦,真棒。”我说。
邦德自豪又兴奋地欢呼着。
然后我继续说:“外面的情况如何?电脑的数据怎么说?你挪一下,我准备好跳下来了!”
邦德的脸色立马变了。这不是他所期待的我完全恢复的样子。
我有着各种各样的疯狂的臆想,以一种最生动的方式,释放着生命里最兴奋的活力。
在我的意识里,我正在为跳伞助跑,准备从距离地面3英里的DC3飞机中跳下……我是最后一名出舱的跳伞员,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位置。
我的身体渴望飞翔。
猛然进入飞机外灿烂的阳光,我立刻为头朝下的自由落体做好准备。在我的意识中,双手在背后握紧,冲向地面的时候,我感受着熟悉的蜂鸣声。我还看见巨大的银色飞机的机身冲向遥远的天际。它巨大的螺旋桨缓慢地转动着,白云和地面在光滑的机腹上被映衬出来。在距离地面尚有几英里的时候,一切都慢了下来,这是为了减少风速对跳伞员的冲击。飞机的轮子也放了下来,就好像要开始着陆一样。看着这奇怪的景象,听着耳边的啪啪声,我沉思着。
在头向下自由落体的时候,我的双手紧握,逐渐加速到每小时220英里。此时,只有蓝色斑点的头盔和肩膀上稀薄的空气,帮助我抵抗下面巨大飞机的拉扯。它每秒移动的距离,比足球场还要长。风猛烈地呼啸着。此时的风速比飓风还要快上3倍,而且伴随着巨大的轰鸣。
穿过两朵巨大而松软的白云之后,我进入了这两朵云之间的缝隙。
绿色的草地和闪亮的深蓝色海洋就在远处。我飞速下沉、急速加入我几乎不可见的伙伴们,形成了五彩缤纷的雪花形状。随着其他伙伴的加入,雪花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我的思维是跳跃的。我在当下,在重症监护室中;我又在别处,正经历着令人激动的华丽跳伞之旅。
我的思维很混乱,似乎正处于疯狂的边缘。
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一直向周围的人嘟囔着关于跳伞、飞机和网状信息的事情。当我的大脑逐渐恢复功能的时候,我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令人疲惫却又充满奇思妙想的状态。当我闭上眼的时候,网状信息就会出现;即使我睁着眼,它们有时也会出现在天花板上。我开始对“网状信息”的丑陋背景着迷。闭上眼睛的时候,我还会听到刺耳的、单调的、令人不舒服的念诵咒语的声响。但一般来说,我睁开双眼,这些声音就会消失。
我不时地将手指指向空中(就像ET那样),试图用俄语或中文引导网状的声响从我身边越过。
总体来说,我有点疯狂。
这一切都很像在地下王国中的经历,但更像是一场噩梦。因为这一切都跟我过去的经历相关。我认出了自己的家人,但我还没记起他们的名字。比如,我连霍莉的名字都没记起。
与此同时,这一切都很模糊,也缺乏生气。
这种感觉完全不像在那扇大门和理想王国中那样清晰。但意识的确是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大脑中。
尽管当我睁开眼的一刹那,眼前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清晰。但很快,我又遗忘了昏迷前我在人世的所有经历。我唯一的记忆只跟昏迷期间的经历有关。我记得那个丑陋、粗糙的地下王国,记得那扇田园牧歌式的大门,也记得满是荣耀光辉的理想王国。我在那里找到的真正的自我意识,正在努力寻找一条回来的路。它要去适应地球上紧绷的、有限的实体躯壳,也要去适应时空之内的界限,还要去适应这里的线性思维,更要去适应语言表达的局限。一周之前,周围一切的存在方式,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从那里回来之后,这一切的外在形式都成了繁冗的累赘。
人的身体以其防御机制为特征,而灵性生活则恰恰相反,要以其开阔性为特色。关于我的归来,为何会遭遇这种妄想和偏执,这是我唯一能给出的解释。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觉得霍莉(我知道她是我的妻子,但还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和医生们正试图杀死我。
我开始做更深层的梦并出现更多的幻想,这些都与飞行和跳伞相关。有时这种梦很长,我参与的程度也很高。在梦境最长、最紧张也最离奇的细节中,我发现自己正在南佛罗里达一家癌症诊所的户外自动扶梯上。扶梯的索轮上,霍莉、两名警察和两名日本武士摄影师正向我追来。
事实上,我正在经历所谓的“加护病房精神紊乱”。对于那些大脑失能很长时间又苏醒的病人来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甚至是可预期的。
这种情况我见证过许多,但从未经历过。而且,个人的体验跟外人看到的非常不同。
现在回想起来,对于噩梦和偏执性妄想来说,最有趣的莫过于这一切都是幻想。这些幻想中有一部分是相当激烈的,比如那个关于南佛罗里达和武士的噩梦,而且梦境让人感到非常惊恐。但梦醒之后,仔细一想,这一切又可以明确地辨认出来:我的大脑被什么东西扰乱了,而它自己正在努力调整回来。在这段时间里,我做的有些梦,令人震惊且异常生动。但最后,与我昏迷时所经历的那种“绝对真实”相比,它们不过强调了梦境的差异性而已。
后来我发现,那些我不断提起的火箭、飞机和跳伞等概念,不过是某种观点的准确象征。因为事实是,我从远方过来,正经历着一次危险的回归。也就是说,我的意识要回到那个曾被抛弃、如今又要继续工作的大脑。我的意识离开身体的那一周,除了用火箭发射,人们恐怕很难想到更好的比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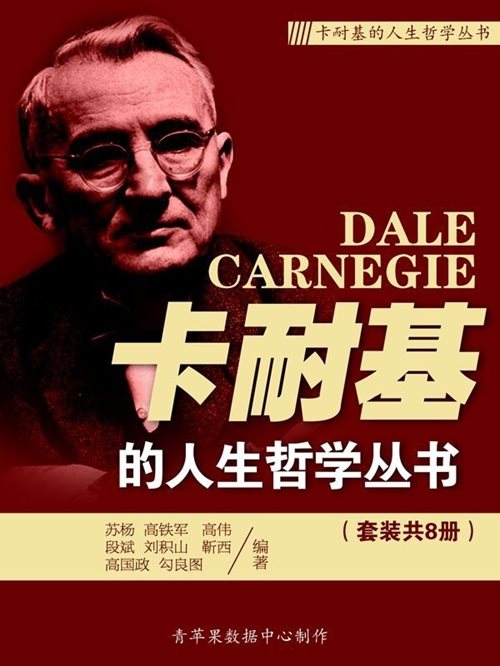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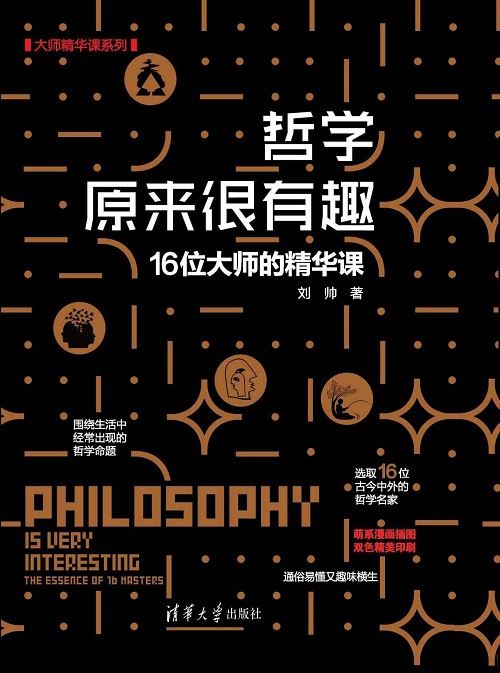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