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我的眼睛睁开了
与韦德医生谈话之前,霍莉让邦德等在门外,因为她不希望有什么坏消息被邦德听到。邦德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但在韦德医生门外徘徊的时候,他听到了医生的只言片语。这已经足够让他了解真实的情况。他心里知道,他的父亲大概永远都不会醒来了。
邦德冲进我的病房,跑到我的床边。他抽泣着亲吻我的额头,抚摸我的肩膀。他掀开我的眼皮,直直地冲着我空洞的眼睛说:“爸爸,你会好起来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他以一种孩子的天真,重复着这样的话,以为说足够多的次数,就能美梦成真。
同时,在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霍莉失神地消化着韦德医生刚刚的那些话。
最后,她说:“那么,我应该给厄本打电话,让他回来。”
韦德医生对此不置可否。
“是啊,我觉得是时候叫他回来了。”
霍莉走到会议室的大落地窗前。透过窗户,能看到被暴风雨洗刷后依然明丽的弗吉尼亚群山。她拿出手机,拨通了厄本的号码。
她打电话的时候,塞尔维亚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霍莉,等一下,”她说,“我先去病房看一下再说。”
塞尔维亚走进重症监护室,站在我的床边。邦德正在揉搓我的手。
塞尔维亚把自己的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轻轻地抚摸着。我已经昏迷了接近一周,我的头轻微地侧向一边。这一周里,大家都看着我的脸,但这张脸对所有人都那么陌生。这一周中,我的眼睛“睁开”过几次:医生在检查我的瞳孔对光的反应(这是检查大脑功能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
的时候,我的眼睛会“睁开”;霍莉和邦德不顾医生的劝阻,扒开我的双眼对我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也会“睁开”。但他们能看到的,不过是我死气沉沉、斜向一侧的眼睛,就像已经坏掉的布娃娃的眼球。
但现在,当塞尔维亚和邦德看着我松弛的脸颊、拒绝接受韦德医生刚刚给出的建议时,有些事情发生了。
我的眼睛睁开了。
塞尔维亚尖叫了出来。她后来告诉我,接下来让她同样感到震惊的,是我的眼睛开始四处观看。上,下,这里,那里……我的这种表现,不像是一个从昏迷中醒来的病人,更像是一个婴儿。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眼睛四处看着,就像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
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的理解是对的。
塞尔维亚从最初的震惊中反应过来,意识到我正被什么力量鼓舞着。她跑出房间,冲到会议室。霍莉正站在落地窗前,给厄本打电话。
“霍莉……霍莉!”塞尔维亚大喊着,“他醒了,醒了!告诉厄本,他父亲醒了!”
霍莉死死地盯着塞尔维亚。“厄本,”她对着电话说,“我必须叫你回来……他……你父亲,醒了……有知觉了。”
霍莉走了几步,然后变成小跑,冲向重症监护室。韦德医生紧紧跟在她后面。他们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床上翻腾着。这种翻腾不是机械的,而是因为我的意识已经回来,感到什么东西让我很不舒服。韦德医生立刻意识到问题所在:呼吸管还插在我的喉咙里。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它了,因为我的大脑以及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生命力。他伸手撕掉了保护胶带,小心地将呼吸管拔了出来。
我的呼吸开始还有些不顺畅。毕竟这是7天以来,我第一次不需要呼吸机的帮助自己呼吸。然后,我说出了7天来的第一句话:“谢谢。”
菲利斯走出电梯的时候,还在回想刚刚看到的彩虹。母亲坐在轮椅里,菲利斯推着她。她们走进房门的时候,菲利斯几乎因为震惊而摔倒在地。我正坐在自己的床上,安好地看着她们。贝特斯正欢乐地跳跃,她冲过来抱住了菲利斯。她们都高兴地流下了泪水。菲利斯走近一些,深深地看着我的眼睛。
我也看着她,然后看着房间里的其他人。我的家人和看护员围在我的床前,对于这种无法解释的转变,依然有些难以相信。我的脸上浮现出平静欢愉的微笑。
“没事啦。”我说,试图将这种回归的欢乐传递给大家。我深情看着他们每一个人,意识到我们之间这种神圣的奇迹。
“别担心……没事啦。”我重复道,想消除他们的顾虑。后来菲利斯告诉我,我说话的方式就像是想要传递给他们一条来自彼岸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彼岸是美好的,我们不用担心任何事情。她说,她经常回想那个瞬间,并被地球思维的局限所困扰;我让他们觉得,我们永远都不会孤单。
当我看着病房里其他人的时候,貌似已经回归了自己的地球身份。
“你们怎么都在这里?”我问他们。
菲利斯回答道:“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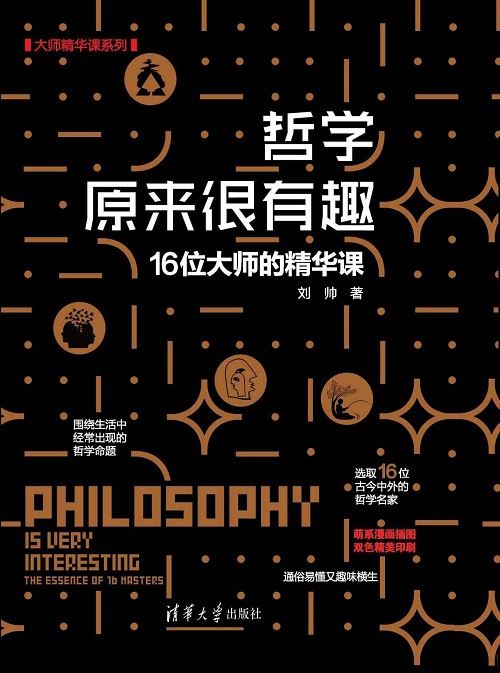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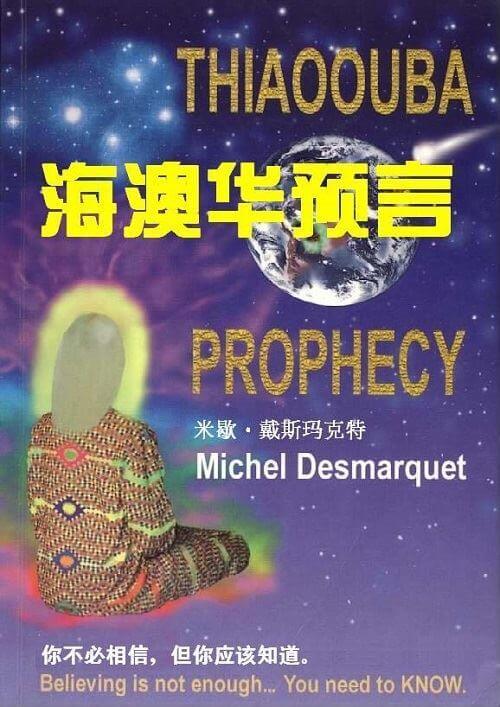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