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头万绪:战斗打响
让我们总结一下21世纪开局时的前方战报:2000年,抗击脊髓灰质炎行动中的进步是令人鼓舞的,这一疾病正在消失的边缘垂死挣扎。不过,世界上还存在多种可令脊灰病毒死灰复燃的源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传染源已经被一一确认,只待时机成熟将它们一一歼灭了。
但是到了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遭遇了不测风云:2000—2001年,一场Ⅰ型脊髓灰质炎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位于加勒比海中,分属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蔓延开来。病毒又在美洲大陆上卷土重来了——本地区早在1991年就宣告过“无脊灰”状态。在这次流行中,多米尼加共和国共确诊并报告了13例脊髓灰质炎病例,海地报告了8例(其中2例死亡)。
2002年4月,亚特兰大脊灰病毒研究参比中心公布了如下结论:“此次流行病中出现的Ⅰ型脊灰病毒株来自1998—1999年的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该病毒经后来与其他肠道病毒的基因重组,重新具有了野生脊灰病毒的特性,尤其是再度具有了致人瘫痪能力和人际传播属性。”换言之,这是一种由口服脊灰疫苗演变而来的野生病毒,在经过至少两年的修炼后,又在接种比例低的人群中造成了一次疾病流行(当地的疫苗接种覆盖率为7%—40%)。
研究员们是如何识破病毒的“猫腻”的?——多亏了病毒基因组测序分析。我们曾在前文讲到,一次疫苗接种行动之后,接种儿童的消化道容易成为病毒繁殖的温床,并且这些病毒会随粪便排出到外部环境中。其他与之有接触的儿童如若没有接种疫苗(伊斯帕尼奥拉岛就是这样),就会被感染,疫苗毒就这样在接种儿童的周围逐渐传播。随着感染的“一传十,十传百”,病毒也会以一定的速度突变,估计相对于原始疫苗毒的遗传趋异率为每年1%。已知演变比例我们就能确定2001—2002年疫情的病毒元凶是何时入侵伊斯帕尼奥拉岛的。
上文提到,病毒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其中的一大部分基因来自肠道病毒,而不是脊灰病毒。肠道病毒怎么也为虎作伥了?之前我们指出,热带地区儿童易感染的其他肠道病毒和口服疫苗中的脊灰病毒会互相干扰,继而降低疫苗的效率。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在一些情况下,接种儿童会遭遇疫苗毒和其他肠道病毒的双重感染,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两种病毒可能会在细胞之中共处一室。当脊灰病毒繁殖时,一种酶会复制它的基因信息,且这种酶在极低的概率下还会发生错误,它可能会错认,在复制脊灰病毒信息的同时连肠道病毒的也一并复制粘贴了。最后,就会形成一种“杂交”病毒——我们称之为基因重组,当然,这种变异后的病毒多为不完整或无法存活的。不过在个别情况下,此杂交病毒会具备繁殖并感染细胞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它还会重新具有野生脊灰病毒的致病性。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疫情就是这么来的。
可能伊斯帕尼奥拉岛不会是唯一一个被恶魔抽中的:其他地区说不定也有覆盖率不够高的疫苗接种行动,这就给了致病性脊髓灰质炎病毒卷土重来的机会。实际上,在此之后,印度尼西亚、埃及、马达加斯加、中国、柬埔寨都发生了新的脊髓灰质炎疫情,其中马达加斯加竟遭遇了两次。缅甸、尼日利亚、尼日尔也在近期发生了脊髓灰质炎流行。
而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三种类型统统在以上疫情中现身,它们的流行时间为1年(中国)到10年(埃及)不等。据估计,埃及有数百万人被口服脊灰疫苗衍生的Ⅱ型脊灰病毒感染,幸而大规模接种行动的推行又挫败了病毒的反攻倒算,遏制住了疫情,令再次出山的病毒又销声匿迹了。
要不是因为对急性弛缓性麻痹病例监测的扩大和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生物学分析,研究员们到2000年还被蒙在鼓里,溯及过往,这只不过是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故伎重施。翻开脊髓灰质炎的流行史,研究员们发现埃及1983—1993年的疫情也是由脊灰疫苗衍生毒造成的。再向前推,1963年的波兰、1963—1966年的白俄罗斯、1980年的罗马尼亚,都因为同样的原因出现过脊髓灰质炎流行。
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口服脊灰疫苗(疫苗毒)在什么情形下容易倒戈,衍生出致病性脊灰病毒。在极其低的概率下(100万—300万次接种中仅有1例),疫苗中的脊灰病毒可能重新具有致病性并导致脊髓灰质炎的发生,我们称这种情况为疫苗相关麻痹型脊髓灰质炎(Vaccine Associated Paralytic Poliomyelitis,vApp)。在具有免疫缺陷的对象体内,疫苗毒能够继续存活并持续多年进行变化,产生致病性病毒(我们称之为免疫缺陷者疫苗株衍生脊灰病毒,即Immuno Deficiency-related Vaccine-derived Poliovirus,iVDPV)。该病毒可诱发严重的脊髓灰质炎病情。而且,由于疫苗接种行动覆盖人群不全面,口服脊灰疫苗衍生病毒可在自然环境中传播多年并与肠道病毒进行重组(我们称之为传播性脊灰疫苗衍生病毒,即Circulating Vaccine-derived Poliovirus,cVDPV)。
传播性脊灰疫苗衍生病毒于近期才为人所知。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的存在是致病性脊灰病毒重现江湖的原因之一,还因为它可能会让脊髓灰质炎消除行动功败垂成,再生变数。实事求是地说,上文中那些疫情发生前,大家还以为口服脊灰疫苗衍生病毒在排出体外后只能存活8—12周。之所以会这么想,一方面是考虑到疫苗中的病毒毒性弱,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古巴的数据。据该国资料记载,当地用灭活疫苗(IPV)取代口服减毒疫苗(OPV)后,20世纪80年代时就实现了疫苗衍生毒在自然环境中的消除。所以人们当时还以为疫苗衍生毒在外界环境中挣扎不了多久就会缴械投降,依据这一认识还制定了消除策略:首先开展口服脊灰疫苗接种行动,至野生脊灰病毒完全消除后停用;然后在野毒完全消除后的两年内继续开展疫苗接种行动,在确认进入“无脊灰”状态之后再对疫苗接种行动“一刀切”。根据在古巴搜集的数据,专家们认为疫苗衍生毒会在疫苗接种行动结束后4个月内自行消失。可惜出乎意料,免疫缺陷者疫苗株衍生脊灰病毒(iVDPV)和传播性脊灰疫苗衍生病毒(cVDPV)跳出来横生枝节,打破了原有计划。
恍然大悟之后,专家们开始苦思冥想——怎样才能实现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实质性消除?结局如何,且看后话。
且让专家们继续探索,而我们则先回到2000年年初。2003年,尼日利亚的情况吸引了各界目光,该国一直是野生脊灰病毒Ⅰ型和Ⅲ型的主要流行地。2002年全世界共报告了677例脊髓灰质炎病例,其中40%出现在尼日利亚,尤以该国北部地区为甚。各方面为遏制疫情付出了极大努力,这不仅是为了抑制病毒的流行——如果病毒再越过国境线,殃及邻国,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就在国家免疫日活动筹备期间,当地宗教领袖却号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穆斯林人士拒绝接种。例如,在2004年2月19日发表的《尼日利亚:穆斯林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怀疑日渐加剧》[19] 一文中,尼日利亚伊斯兰教法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for Sharia in Nigeria,SCSN)主席达迪·艾哈迈德(Datti Ahmed)博士就声称:“我们认为,当代的希特勒分子们别有用心地在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中混入了绝育药和其他病毒,比如导致艾滋病的人免疫缺陷病毒(HIV)。”这之前还有一个导火索,更是引爆了当地人的抵触情绪——美国制药商辉瑞(Pfizer)公司被指控在未告知家长风险的情况下进行了脑膜炎双球菌用药实验。于是当地群众对西医的怀疑与日俱增,村子的首领们也听从了宗教领袖的建议,“宁可出现几个脊髓灰质炎病例,也不能让我们的女性绝育”,卡诺州的州长如是说。而该州正是尼日利亚脊髓灰质炎疫情的中心地带。
世界卫生组织求助于尼日利亚行政当局。于是尼日利亚国民议会就此事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并最终得出脊髓灰质炎疫苗不存在风险的结论,建议继续开展疫苗接种。而伊斯兰教法最高委员会的宗教领袖反驳了这些结论并声称脊灰疫苗接种醉翁之意不在酒,里面的微量荷尔蒙(雌二醇)就是意在令当地人群不育。于是世界卫生组织请求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OIC)、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AU)和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LAS)的负责人说服当地宗教团体。然而,“拨乱反正”并非易事。最终,脊髓灰质炎根除项目团队与伊斯兰最高教法委员会达成妥协:疫苗交由另一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的Biofarma实验室供应,该生产商为这些疫苗的纯净度负责。实际上,Biofarma已经生产了多年脊髓灰质炎疫苗,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UNICEF)的主要疫苗供应商之一。事情终于又走上正轨了。
不过,该地区的抗击脊髓灰质炎计划还是因此而中断了16个月,影响严重。2003年年底,尼日利亚统计到355例脊髓灰质炎病例,而到了下一年年底,这一数字骤升至792,占全球总数(1265例)的63%。更严重的是,Ⅰ型脊灰病毒经由尼日利亚重新扩散到了18个已宣告“无脊灰”状态的国家。到了2004年3月,有10个非洲国家都报告了脊灰病例,其中不仅有尼日利亚的邻国(尼日尔、乍得、喀麦隆、贝宁),更远的国家也被波及(苏丹、科特迪瓦、博茨瓦纳)。本来脊髓灰质炎歼灭战的成功已经近在眼前,却因此次尼日利亚北部接种行动的中断而功亏一篑。2004年5月,紧急行动计划上马,将为非洲21个国家的7400万儿童接种疫苗。虽然计划呕心沥血且花费颇巨(据估为4.5亿美元),可是2005年,其中的19个国家还是报告了1979例脊髓灰质炎。
此事刚刚尘埃落定,正逢多事之秋的尼日利亚又一次成了世界卫生组织关注的对象。2007年9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疫情周报》(Weekly Epidemiological Record ,WER)刊出一篇文章,称脊髓灰质炎Ⅱ型病毒正在该国北部肆虐。文中指出,该病毒源自口服脊灰疫苗,是传播性脊灰疫苗衍生毒(cVDPV),于2006年9月在当地被发现。
2006年1月1日—2007年8月17日,在尼日利亚北部9个州的弛缓性麻痹患儿中共确诊69例脊髓灰质炎。似曾相识,出现这些病例的根源还是在于——疫苗接种行动覆盖率太低,没能对病毒布下天罗地网。
2006年的疫情,为何等到2007年才公之于众呢?专家们解释说,这实在是为了不影响疫苗接种行动的权宜之计。本来疫苗接种已经令当地物议沸腾,而这次又是疫苗衍生毒惹起的祸端。在2003年的“事件”之后,尼日利亚在抗击脊髓灰质炎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只剩下Ⅰ型和Ⅲ型脊灰病毒还在负隅顽抗。不过疫苗接种覆盖率仍然不够高:2005年,该国北部的覆盖率依然不足50%;到了2006年,尼日利亚还有6%—30%的儿童从未服用过口服脊灰疫苗。传播性脊灰疫苗衍生毒(cVDPV)恰恰是钻了接种不足的空子。
调查披露,实际上Ⅱ型脊灰病毒从2005年起就开始招兵买马、流窜各地了。虽然有各个接种行动的反击,但2009年7月为止共统计到124例脊髓灰质炎病例——疫情依然猖獗。我方甚至有人认为疫源地的防守已然失控,Ⅱ型脊灰病毒有可能会突围至其他地区。虽然真实情形还没有这么严重,但有一个事实无法逃避:不管是从自然环境中的传播模式还是从临床症状来看,这一口服脊灰疫苗衍生毒就如同野生病毒一般。不管来自何方,Ⅱ型脊灰病毒的的确确又在尼日利亚死灰复燃了。
同之前的几次流行一样,这次疫情再次警醒人们,要打赢脊髓灰质炎歼灭战,必须攻坚——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Ⅰ型、Ⅱ型和Ⅲ型统统赶尽杀绝。此外,除传播性脊灰疫苗衍生毒(cVDPD)的情况外,我们还在中等收入国家,如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叙利亚、伊朗、泰国发现了免疫缺陷者脊灰病毒(iPVDV),症状显示为长期慢性感染(3年以上)。
鏖战至此,世界卫生组织又会想出什么制胜良策呢?答案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要研发抗病毒新药,在慢性感染者的体内消灭脊灰病毒;另一方面,要在Ⅰ型和Ⅲ型野生脊灰病毒肆虐的四国——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日利亚——加强火力,增加疫苗接种行动场次。要知道,这四国是仅剩的脊髓灰质炎流行国了,必须拔掉病毒最后的堡垒:Ⅱ型野生脊灰病毒多年前已经消失(可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现存的Ⅱ型是疫苗衍生毒。其他国家报告的病例都是这四个流行国输入的。
为什么这四国的战斗还无法结束呢?印度的情况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可说是困难重重,还不具备向病毒发动“总攻”的条件。印度接收的儿童口服疫苗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还有国家免疫日助力,但是仅该国报告的病例就占了全球的50%。为什么会这样?——当地的人口密度和卫生状况都助长了脊灰病毒的气焰。而且肠道病毒在热带地区也更为猖獗,它们动辄就会诱发腹泻,干扰口服疫苗,大大降低疫苗的效力。
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比哈尔(Bihar)是印度最受疫情影响的两个州,它们都位于该国北部与尼泊尔接壤的地带。疫情调查显示,虽然两地的孩子都多次服用了脊灰疫苗(平均每个孩子15剂次三价口服疫苗),但当地5岁以下儿童中只有71%获得了针对Ⅰ型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有效免疫保护。鉴于情势反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5年决定调整接种策略,除原有的三价口服脊灰疫苗(含有3种类型病毒)外,再加种单价Ⅰ型口服脊灰疫苗(即只含有Ⅰ型病毒)。口服脊灰疫苗的投入使用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人们就发现单价疫苗的效力最高。实际上,服用了三价疫苗后,3种病毒共存于消化道中,难免互相干扰,反而降低疫苗的效率。
Ⅰ型单价疫苗自2005年起在埃及应用以来,便大获成功。该国的病例是由来自其他流行国的输入性病例引起的。单价疫苗在印度也会无往不利吗?2006年,北方邦爆发了一次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借机比较了Ⅰ型单价疫苗和三价疫苗的效力,结论如下:单价疫苗的战斗力比三价疫苗高三倍(这里的效力是针对单价疫苗所含的那种病毒)。不过高效也是相对的:至少要5剂单价疫苗才能使80%的孩子对Ⅰ型脊灰病毒获得保护。在2010年10月的《柳叶刀》杂志上,世界卫生组织披露了在印度测试双价疫苗(Ⅰ型和Ⅲ型脊灰病毒)的效果,看起来十分令人鼓舞。于是在不断努力下,我方终于为发动“最后的进攻”开辟了战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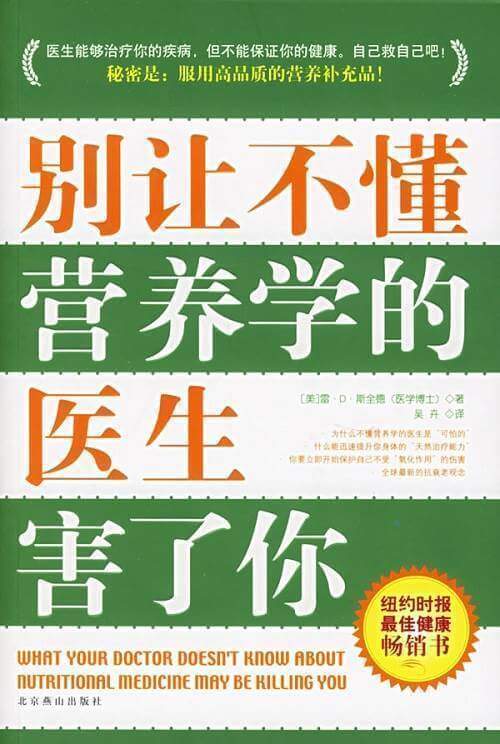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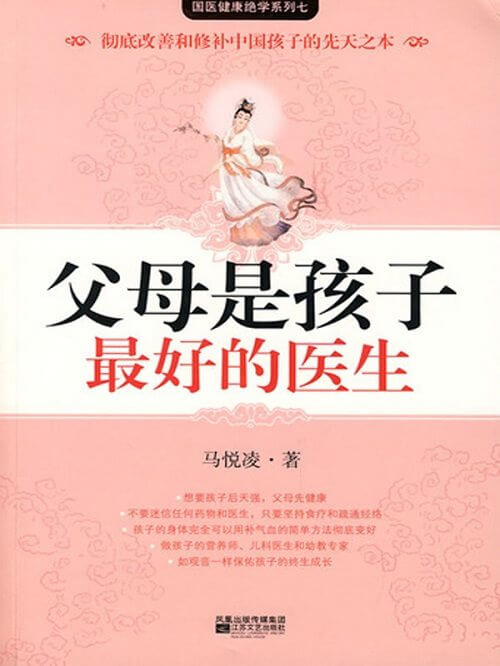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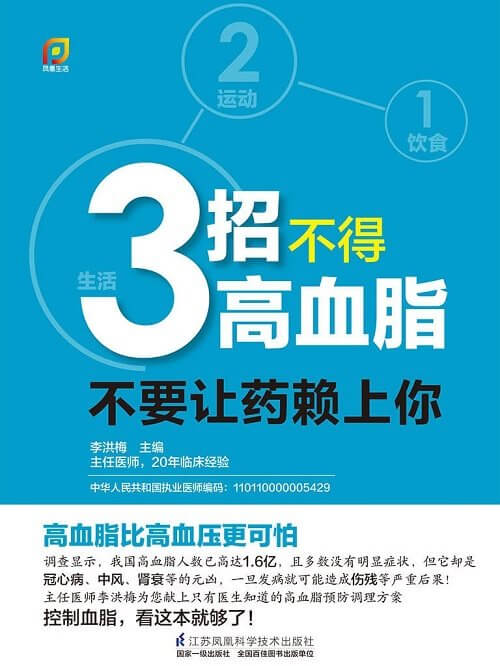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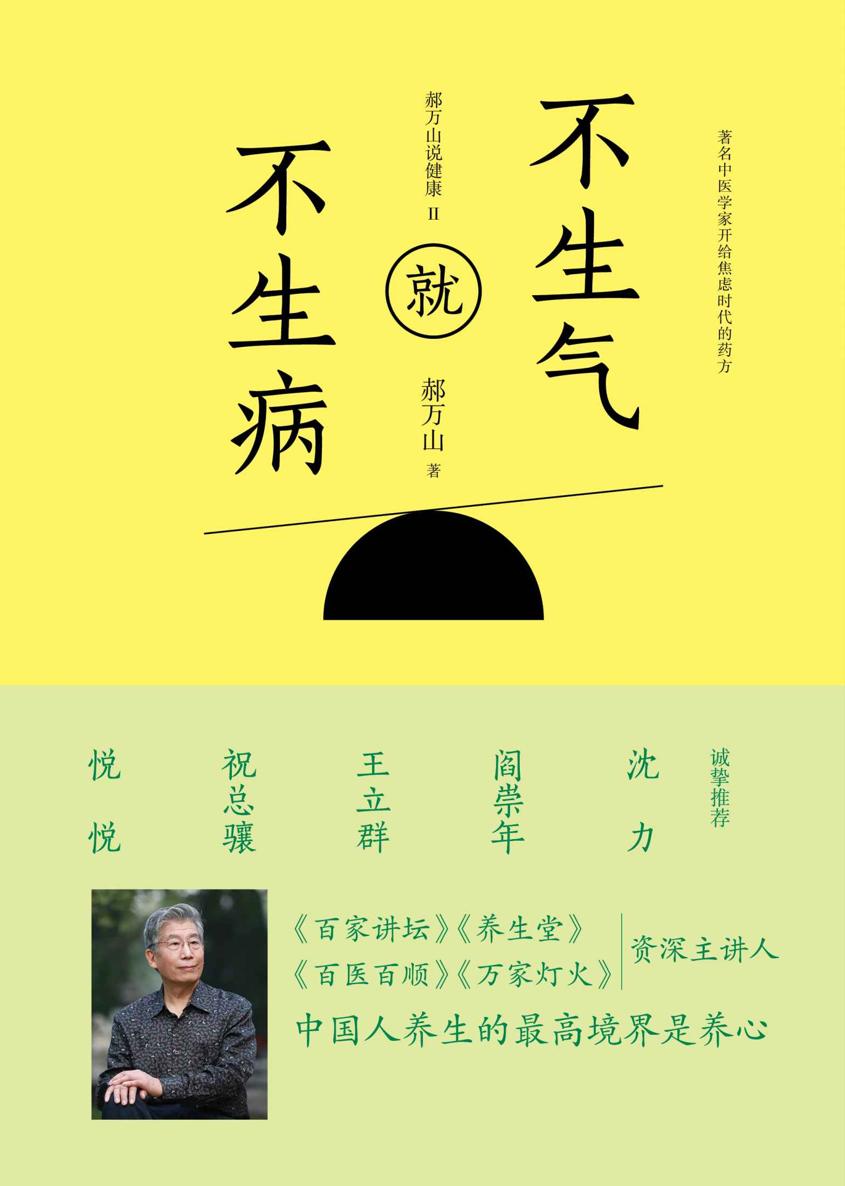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