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从未有过的完整
在接下来的7年中,我的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都没有走出这件事的阴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身边的人,甚至是最亲密的家人,都不能确定导致我发生改变的原因。不过渐渐地,通过我日常的言谈,霍莉和我的姐妹们还是明白了事情的根由。
2007年,我和家人去南卡罗来纳的海边度假。某天清晨我们在沙滩上散步的时候,贝特斯和菲利斯挑起了这个话题。“你有没有想过给你的生父生母再写封信试试?”菲利斯问。
“是啊,”贝特斯说,“说不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呢。或许你只是不知道而已。”那时候,贝特斯正准备收养一个孩子,所以听到她说起这个话题我一点儿都不吃惊。但我那一瞬间的反应就是:不,我没办法再经历一次!当然这只是我的心里话,并没有说出来。我依然清楚地记得,7年前遭到拒绝时,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打击。我知道贝特斯和菲利斯都是出于好意。她们知道我很痛苦,也知道这痛苦的来源,她们想帮我走出困境,让一切都回到正轨。她们向我保证,不管发生什么都会陪我一起经历,不会让我感到之前的那种孤单。我们始终是在一起的。
所以2007年8月初,我给自己的亲妹妹写了一封匿名信。她是唯一能帮我处理这件事的人选。这封信我送到了儿童之家的贝蒂那里。
亲爱的妹妹:
我很高兴终于跟你、我们的弟弟和父母联系上了。在和我的养母以及我现在的姐妹长谈之后,她们也支持我写信给你们。对于我想更多了解自己生身家庭的渴望,她们也非常了解。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9岁,一个19岁。他们对自己的宗源也很有兴趣。如果在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家里的事情,我和我的妻儿都会非常感激。对我来说,我们的父母从年轻到现在有过怎样的经历是我最想知道的。你们大家的性格又如何呢?
我们年纪也都大了,我特别希望能跟他们见上一面。所有的安排都可以商量。对于你和父母想要保证的隐私,我既非常尊重,也非常理解。收养我的家庭对我很好,对于父母当年将我送养,大家也都非常理解。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决定,或者决定告诉我多少,我都表示十分的敬意。
你对此事的考虑和态度,我也一定会理解和支持。真的非常感谢。
再次对你致以真诚的谢意。
你的哥哥
几周之后,我收到了儿童之家寄来的信。这封信是我妹妹写的。
“是的,我们也很想见到你。”她写道。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禁止她透露关于自己身份的任何信息,但她还是尽力向我描述了我的生身家庭的许多细节。这是我第一次对这个我从未见过的家庭了解这么多。
她说我的生父曾在越战中做过海军飞行员,这一点让我大感震惊,怪不得我一直喜欢飞机和跳伞。让我感到更加惊奇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阿波罗计划中,父亲曾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受训。其实1983年的时候,我自己也曾考虑过接受训练成为一名专业的航天飞行员。后来,我生父一直在泛美航空公司做飞行员。
2007年10月,我终于与自己的生身家庭见面了。我的父亲理查德、母亲安、妹妹凯西和弟弟大卫都来了。母亲告诉我,1953年她在佛罗伦萨的克里腾顿之家住了3个月,那个地方就在夏洛特纪念医院旁边。那里所有的女孩儿都有自己的代号。因为喜欢美国历史,我的母亲为自己取了弗吉尼亚·达尔的代称。这个名字也是新世界英国移民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在那里,人们都叫她达尔。那时她16岁,是所有女孩中最小的。
母亲还告诉我,她的父亲在得知她的“窘境”之后,很乐意为她提供帮助。他甚至想过把我带回去并搬家。但那时他已经失业一段时间了,把一个婴儿带回家显然会是很大的经济负担,更别提其他各种可能的问题。
他一个很亲密的朋友曾说起,在南卡罗来纳的迪伦有一名医生,可以帮他把孩子送走。但她的母亲根本不想听到这些。
母亲告诉我,那是1953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她一个人走过空荡荡的大街,天上是被风吹得零散的云,耳畔是阵阵疾风。她仰望天空,星辰在闪烁。这一刻她希望能一个人安静一下。除了月亮、星辰和即将出生的我,她不需要任何陪伴。
“新月低低地挂在天空西侧,灿烂的木星逐渐升起,整夜都注视着我们。你父亲很喜欢科学和天文学,后来他告诉我,其实那天木星在相反的方向,而且已经有9年没这么亮过了。那一刻之后,我们的生命中会有更多事情发生,包括另外几个孩子的出生。但那时,我只是觉得行星之王那么漂亮、那么明亮地注视着我们。”
当她走进医院门厅的时候,一种神奇的想法出现在她的脑海。在克里腾顿之家,女孩儿们生产之后一般会待两周,然后回家继续之前的生活。如果母亲那天夜里生下我,而且两周后别人肯放她回家的话,她就能带我回家过圣诞节了。多美妙的奇迹啊,在圣诞节带我回家。
“克劳福德医生刚刚为另一个孩子接生完,看上去很累的样子。”母亲继续说。他把一块浸了乙醚的纱布盖在她的脸上,缓解生产带来的疼痛。所以当她在凌晨2点42分生下我的时候,其实处于半清醒状态。我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母亲告诉我,她当时那么想拥抱我、爱抚我,还说永远都记得我的啼哭声,但疲倦和麻醉剂最终让她控制不住地睡去了。
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火星、土星、水星以及灿烂的金星依次出现在东方的天空,迎接我来到这个世界。同时,我的母亲正沉沉地睡着。她已经几个月没能好好休息了。
天亮之前,护士叫醒了她。
“有个小家伙要跟你打个招呼。”她高兴地说,然后把包在天蓝色毯子里的我抱到母亲面前。
“护士们都说你是整个婴儿室中最漂亮的孩子。我骄傲极了。”母亲说。
尽管母亲非常想把我留下,但冰冷的现实逼迫着她做出更理性的选择。理查德梦想着去读大学,可这个梦想无法为我提供食物。或许那时我感受到了母亲的痛苦,开始拒绝进食。我出生第11天的时候,我的健康情况令人担忧。所以人生中的第一个圣诞节以及接下来的9天,我都在夏洛特的医院里度过。
把我托付给医院之后,母亲坐了两小时的公车回到她家所在的那个小镇。她和自己的父母、姐妹、朋友一起欢度了那个圣诞节。她已经3个多月没跟他们见面了。那个圣诞节所有的画面里都没有我。
等我再次进食的时候,我独自的生活也即将开始。母亲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失去了对我的主动权,而且医院不会允许她把我带走。
新年之后,当她给医院打电话的时候,人们告诉她,我已经被送去格林斯伯勒的儿童之家。
“就这么送走了?太不公平了!”母亲说。
接下来的3个月,我跟其他几个婴儿在一间婴儿室里度过。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母亲没有办法抚养的弃儿。儿童之家是一个蓝灰色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是由社会捐建的。我的婴儿床在二楼。“作为你的第一个家,那个地方还算不错。”母亲边笑边说,“尽管那里实际上就是个婴儿宿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她不止一次地坐3个小时的公车来看我,绞尽脑汁地想知道怎样才能把我带回家。她的母亲和理查德都曾陪她去看过我,护士只允许她透过窗户看我,不允许她进入房间,更不可能允许她抱我。
直到1954年3月底,情况越来越明朗,事情不可能朝着她想的方向发展了。她不得不放弃我。最后一次,她和自己的母亲坐公车来到格林斯伯勒。
“我必须看着你的眼睛告诉你,向你解释这一切,”母亲对我说,“虽然你只是咯咯地笑、嘴边冒着泡、欢快地叽里咕噜着,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我觉得必须给你个解释。我最后一次紧紧地抱着你,亲吻着你的耳朵、脸颊和胸膛,轻柔地抚摸着你。我用力地呼吸着你身上怡人的婴儿气息。这一切都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我轻轻叫着你的奶名,‘我真的好爱你。你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我会永远爱你,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说‘上帝,请让他知道是有人深切地爱着他的,而且这份爱一直都会在’。但我不知道我的祈祷是否会被听见。20世纪50年代的领养政策是不可更改的,而且是保密的。没有回头路,也没有任何解释。在交接文件上,人们甚至会更改孩子的出生年月,以防有人按图索骥地发现孩子的真实身份。孩子被领养之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和线索。领养信息在法律严格的保护之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遗忘这一切,去继续自己的生活,并且从中吸取教训。
“我最后一次亲吻了你,轻轻地把你放回婴儿床。我把你包在小小的蓝色毯子中,最后看了一眼你蓝色的眼睛。我轻吻了一下自己的手指,然后把手指放在你的额头。
“‘再见了,理查德·迈克。我爱你。’这是50多年前我最后对你说的话。”
安还告诉了我后来发生在她和理查德之间的事情,包括他们的婚姻、其他孩子的诞生。其实她一直都很想知道我后来的情况。理查德除了海军飞行员和客机飞行员的身份外,还有一个律师的身份。安觉得,作为律师的理查德或许可以找到我。但理查德太绅士了,他无法打破1954年达成的领养协议,所以一直置身事外。20世纪70年代,越战正打得火热的时候,安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1972年12月我刚好19岁,她很担心我会应征入伍,如果我去打仗又会遭遇什么样的情况?事实上,那时我考虑过去参加海军陆战队,只是我无法满足部队对视力的要求。当时有人说,就算我的视力不达标,海军陆战队也会招收我们。不过后来战事逐渐缓和,所以我并没有入伍。相反,我进了医学院。但安对于这一切一无所知。1973年春天,他们看到幸存的越战战俘从越南北部的“河内希尔顿”监狱乘飞机返回。他们认识的那些飞行员的牺牲,让他们心痛不已。实际上,我父亲所在的突击队有一半人都没能回来。所以安觉得,或许我已经在越战中牺牲了。
这种想法一直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她都相信我已经惨死在越南的稻田之中。如果那时候她知道我正在教堂山,离她不过几英里的话,一定会非常震惊吧。
2008年夏天,在南卡罗来纳的林奇菲尔德海滩,我和生父理查德、他的兄弟鲍勃以及他的妹夫(也叫鲍勃)见了面。我的叔父鲍勃在朝鲜战争中曾被授勋,还是“中国湖”(位于加利福尼亚荒原的海军武器测试中心,在那里他完善了“响尾蛇”导弹系统,并驾驶过F-104星级战斗机)的一名试飞员。而我的姑父鲍勃,在1957年的“追日行动”中创造了新的速度纪录。“追日行动”是一个驾驶F-101巫毒喷气式战斗机的比赛,参赛者要以平均每小时1000英里的速度绕地飞行。
这让我有一种类似旧友团聚的感觉。
与我生身父母的会面,预示着我与自己“未知部分”的告别。后来我发现,分别的这些年月不仅是我的痛,也是他们最大的痛。
只有一个悲伤永远无法弥补,那就是10年前我的亲妹妹贝特斯的去世。是的,她的名字跟我养父母的女儿一样,而且她们的丈夫都叫罗伯斯。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每个人都告诉我,贝特斯有一副热心肠,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强暴危机援助中心度过。在这里的工作结束后,人们发现她经常去喂养流浪猫狗。“她是一个真正的天使。”我的生母安说。
凯西答应会寄一张贝特斯的照片给我。跟我一样,贝特斯也曾陷入酒精的困扰。看到她最后的结局,想起自己当时的各种纠结,我再一次庆幸自己戒除了酒瘾。我多么希望之前就认识贝特斯啊。那样我会安慰她,告诉她一切伤痛都会抚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在与我的生身家庭会面之后,我的生命里第一次感觉生活还可以更好的。家人是最重要的,我找回了自己的家人——至少是大部分家人。这也使我第一次深刻地发现,人的宗族血脉会以如此奇特的方式治愈人的一生。了解了自己从何处来之后,也给了我重新接纳自我、审视梦想和激发自我潜能的机会。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最终抛弃了一直紧随我的那些疑虑——那些关于自己根源的疑虑,那些自己是否被爱与珍视的疑虑。之前,在我的潜意识中,我似乎觉得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甚至觉得自己不该来到世上。而发现了自己一直被爱包围之后,我最深刻的创伤逐渐也愈合了。我体验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完整。
这并不是这次旅程中唯一的发现。那一天,我和厄本在车里时,以为已经得到了关于上帝问题的答案。世界上真的有爱我们的上帝吗?但现在,在我的意识中,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是:没有。
在我持续7天的昏迷中,我又重新想起了这个问题。但是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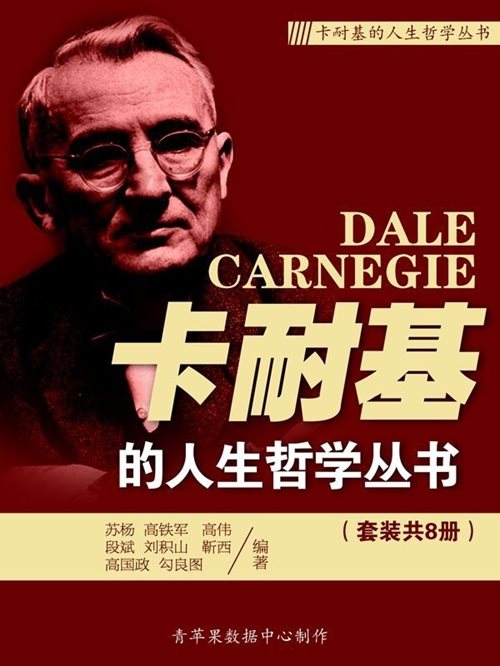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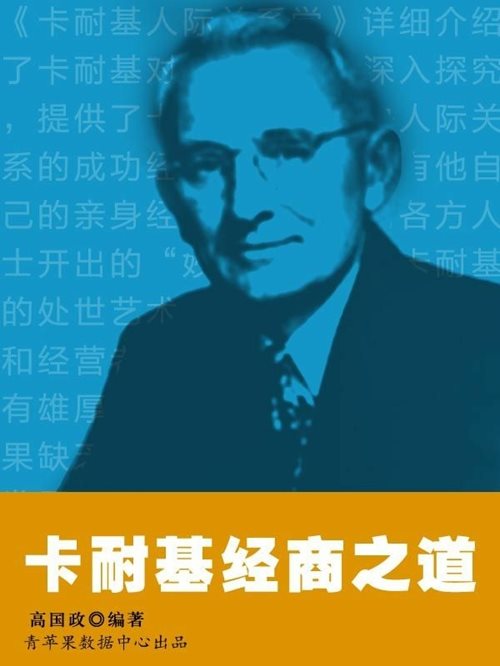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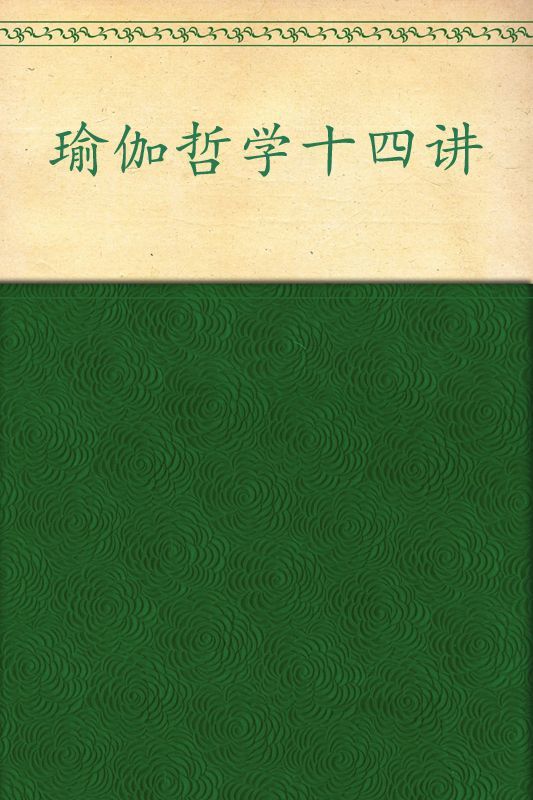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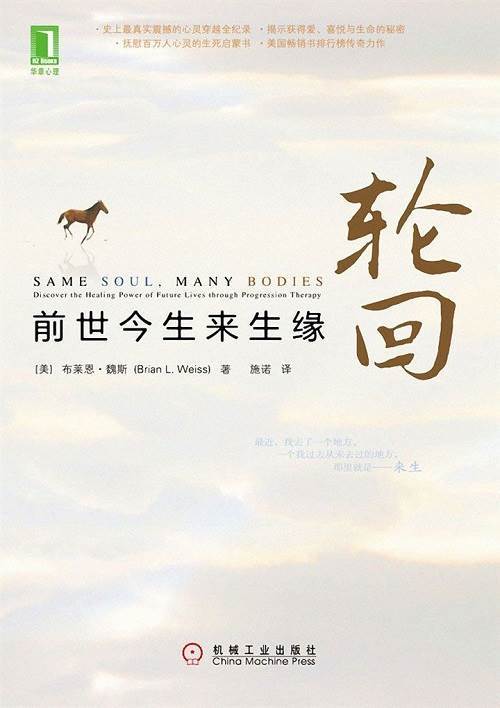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