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
雷布思是因为无聊才打的电话。然而,他和克拉克讲电话还不到一分钟,就看到一辆黑色的大众高尔夫轿车咆哮而来,停在停车场外面路边的车站。从车里出来个女的,正是卡思·米尔斯。因此,雷布思只能匆匆挂了电话。
“米尔斯小姐吗?”他说着,朝她走去。傍晚,夜色渐深,从北海吹来刺骨的风。他不知道自己期待“里普尔”穿什么来,也许是一件长披肩。事实上,她当时穿的更像一件派克大衣,风帽带着鼬皮边儿。她30多岁,个子很高,红色秀发呈小卷,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她脸色苍白,脸盘圆圆的,涂着唇膏,看着一点都不像雷布思口袋里照片上的那个人。
“您是雷布思探长吗?”她猜测道,并和雷布思简单握了个手。她戴着驾驶用黑色皮手套,握完手就把手伸进口袋里了。“我很讨厌每年的这个时候,”她咕哝着,抬头看了看天空,“早上起床时天还没亮,晚上回家时天又黑了。”
“你每天都按时上下班吗?”雷布思问。
“干我们这行的总会有事情需要去处理。”她看了最近的出口栏杆处那个“故障”标志牌一眼。
“你上周三晚上外出了吗?在这附近转悠了吗?”
她仍旧盯着出口栏杆看,“我记得当晚是9点到的家。坎宁街上有个设备出了问题,接班的人还没来,我让助理安了个双倍设备,就这些。”她将注意力缓缓转向雷布思,“你是在问那名男子遇害当晚吧。”
“没错。只可惜你们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一点用场都派不上……不然我们也能得到一些有用信息。”
“我们安装它的时候,可没想过会出现谋杀场面。”
雷布思没理会这句话。“这么说事发当晚10点左右你并没有碰巧路过这里?”
“谁说我路过了?”
“谁也没说。只是我们这里有个女子长相描述很符合你……”好。他直击主题了,想看看卡思会有什么反应。只见她眉头一皱,双臂交叉在胸前。
“我倒想先问问你是怎么得知我长什么样的?”她问道,并朝着停车场瞟了一眼,“是哪个伙计下班就撒谎?我得看看到底是谁这么不老实。”
“事实上他们只告诉我你有时会戴风帽。有位路人当晚碰巧看到有个女的在这里逗留,而且她也戴着风帽……”
“有个戴风帽的女的?冬夜10点钟?你就是这么缩小嫌疑范围的?”
突然,雷布思很想让这一切赶紧结束。他想坐在酒吧高凳子上喝饮料,把其他事情都抛之脑后。“假如你当时不在场的话,”他叹了口气,“直接告诉我就是了。”
她听了这句话思索了片刻。“我不太确定。”最后她说道,拖得很长。
“你这话什么意思?”
“假如我成了某个案子的嫌疑人,或许会很有意思……”
“谢谢。事实上还真有很多人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情节严重的会被我们起诉。”他补充道。
卡思脸上浮现出笑容。“对不起,”她道歉说,“这一天太漫长了,累得我筋疲力尽,或许我开玩笑找错对象了。”她的注意力再次转向出口栏杆处。“我觉得应该去和加里谈谈,免得他忘了通报故障。”她撩起其中一只手套看了看手表。“今天的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她又将目光转向雷布思。“完了我可能会去蒙彼利埃。”
“布伦茨菲尔德酒店的酒吧吗?”雷布思很快就猜到了这个地方。
她笑得更灿烂了。“你看着就像是知道这种地方的人。”她说。
最后,他在那里喝了三杯,都怨“第三杯免费”促销活动。他喝的不是别的,三小杯进口淡啤酒下肚,还没到神智不清的地步。卡思·米尔斯很能喝,她那三杯酒加起来足足够一瓶里奥哈葡萄酒了。她把车停在角落里,因为她就住在附近某个公寓里,因此车一晚上都可以停在那里。
“别想把我灌醉,让我醉酒驾车。”她摇摇手指说。
“我也打算走着回去。”他告诉她自己的公寓在马奇蒙特街。
他走进酒吧时音乐很响,还有一些人在聊天。他看到卡思在酒吧靠里面的一个位子等着他。
“你坐这么靠里,难道不想让我找到你吗?”他猜测道。
“我只是不想让你那么容易找到我。”
他俩谈的大多是关于雷布思的工作,还有爱丁堡一些日常事务——交通状况、道路施工、议会、感冒等。她说自己没什么私生活可言。
“我18岁嫁人,20岁就离婚了;34岁又结了一次婚,只持续了6个月。我第二次结婚前就应该清楚长久不了,对吧?”
“不过你也不可能一直都是停车场主管吧?”
当然不是。她先是在办公室打杂,紧接着开了个咨询公司,两年半后开不下去了,尽管第二任丈夫想用自己的存款帮她忙,却也没帮上。
“之后我成了一名私人助理,但是适应不了那种工作……有一段时间我是靠救济金过日子的,其间一直在接受培训。这才当上了现在的主管。”
“干我们这行的,”雷布思说,“经常能听到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总会隐瞒有趣的方面。”
“那你拷问我吧。”她说着,伸了伸胳膊。
终于,在他的竭力逼问下,她谈到了一些有关加里·沃什和乔·威尔斯的事情。她也怀疑威尔斯上班时喝酒,但是没当场逮住过他。
“身为侦探,你应该帮我这个忙。”
“你需要找个眼线,或者可以瞒着他再安装几台闭路电视监控摄像头。”
她一听这话大笑起来,然后请服务员把那杯免费酒端给她。
一小时后,他们看了看各自的手表,相视一笑。“你呢?”她问。“有没有找到愿意迁就你、和你一起过日子的人呢?”
“现在还没有。我之前结过婚,有个女儿,现在30多岁了。”
“你没遇到过什么办公室恋情吗?工作压力这么大,又在一起工作……我能想象得到会是什么感觉。”
“我没遇到过。”雷布思肯定地说。
“你真行。”她嗤之以鼻,嘴角抽动了一下,“我算是差不多放弃一夜情了。”说完,她笑了。
“这样很好啊。”他说完又觉得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
“你要是和一名嫌疑犯鬼混的话,不会惹上麻烦吗?”
“又没有人举报,对吧?”
“没这个必要。”她指着酒吧内部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摄像头说。只见那个摄像头位于天花板角落里,直冲着他俩。他们看了一下都大笑起来。她开始穿那件派克大衣。这时,他又问:“当晚你在那里吗?跟我说实话……”她摇摇头,他也知道肯定又是这个答案。
两人走到外面后,他递给她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的手机号。两人既没有亲吻告别,也没有握手再见。他俩在情场上都已经伤痕累累了,因此非常尊重彼此。雷布思在回家的路上买了点炸鱼和土豆条,装在硬纸盒里。考虑到健康,这类食品不再用报纸包装了。不过现在吃起来味道却不一样,也没有鳕鱼了。这都怪北海的过度捕捞。鳕鱼很快就会成为稀有的美味佳肴,不然的话就可能濒临灭绝。到了公寓时,他已经把那包吃完了,于是开始上楼。没有收到邮件,连账单都没有。他打开起居室的灯,选了几首歌播放,然后给西沃恩打了个电话。
“有事吗?”她问。
“你觉得我们接下来该如何行动?”
“我正想着去冰箱拿罐吃的呢。”
“刚才我本来就想说这个呢。”
“时代在变化。”
“我也正想这么说呢!”
他听到她在那边大笑。然后她问今天采访卡思·米尔斯结果怎样。
“又是个死胡同。”
“那你也花了不少时间啊。”
“我觉得没必要回局里去了。”他停顿了一下,“你想向上级告发我,说我不会掐时间吗?”
“你猜呢?你听什么音乐呢?”
“《小罪犯》(Little Criminals)。其中有一首歌叫《乔利·科珀斯在游行》(Jolly Coppers on Parade)。”
“这么说不是警察熟悉的人……”
“兰迪·纽曼(Randy Newman)。我还喜欢他另外一首歌:《你糊弄不了胖子》(You Can't Fool the Fat Man)。”
“有没有可能这个胖子就是你呢?”
“不如我也让你猜猜。”两人都沉默了一阵,“你开始支持麦克雷了,对吧?你也觉得我们应该集中关注那些抢劫犯档案,是吗?”
“我让菲尔和科林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克拉克说。
“你丧失信心了吗?”
“我信心满满。”
“好吧,我说错了……谨慎点没错。我不会怪你。”
“约翰,你想想。难道托多罗夫从加里东尼亚宾馆一出来就被人跟踪上了吗?闭路电视监控摄像头显示并非如此。难道有街头女郎向他求欢了吗?或许,或许他很轻易就从了呢。不管发生了什么,这位诗人是在错的时间出现在了错的地方。”
“这一点我也基本同意。”
“从麦克法兰的话里可以看出,俄国商业巨头和阿尔贝纳奇第一银行也给我们提供不了什么线索。”
“不过这很有意思,不是吗?假如你的工作没了乐趣,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约翰,只有你觉得有意思……你一直都这么认为。”
“既然这是我最后一周上班了,那就迁就我一下吧。”
“我觉得我已经很迁就你了。”
“不,你现在是在挤对我。你让托德·古德耶尔插手正说明了这一点,他是你的二号人物,而之前你刚好也是我的二号。你已经开始培养他了,或许还很享受这个过程。”
“等一等……”
“我猜他也是你达到目的的手段吧。只要他在你身边,你就不需要在菲尔和科林之间做出选择。”
“难怪你从来都没能高升。原来你会这么想。”
“克拉克,至于高升,你每往上爬一级,就会出现其他需要你巴结的人。”
“你说的可真形象。”
“生活就需要一些诗情画意。”他跟她说明天见——“我一直认为你会需要我。”——说完他挂了电话。他坐在那里等了5分钟,心想她会不会回个电话,但是她没有。兰迪·纽曼的曲子很活泼,于是雷布思关掉了音乐。他本可以播放许多悲情的曲子,比如早期的克里姆森国王(King Crimson)或者彼得·哈米尔(Peter Hammill)。然而,他却没再听别的音乐,而是在寂静的公寓里来回踱着步,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最后来到前厅,手里拿着萨博车钥匙。
“为什么不呢?”他扪心自问。他这样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认为这会是最后一次。他还没醉得不成样子,因此开车应该不成问题。他锁上公寓,朝楼梯井走去,消失在夜色中。他打开车门,上了车。开车去那里只需要5分钟。他再次路过蒙彼利埃,在布伦茨菲尔德向右拐,然后再向右拐。之后,他把车停在维多利亚时代房屋附近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他经常来这里,还注意到了一些变化:路灯柱换成新的了,人行道油漆也是新刷的。有几个警示性标志,上面写着明年3月份停车场就要分区了。马奇蒙特街那边已经开始分区了,可是想找个空车位还是那么难。有几辆运送垃圾的车来来往往。他还听到工人讲的波兰口音。有一些人家扩展了地盘,车库被分割成两个独立花园。白天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到了晚上却非常寂寥。事实上,每家每户都有私家车道,但是临近街道的车子可以在这里过夜。没有人注意过雷布思。事实上,有位遛狗的人以为他也住在这附近,每次见到他总会朝他点头微笑,或者打个招呼。他那条狗很小,瘦长瘦长的,看上去不怎么信任雷布思。有一次雷布思蹲下身子来想拍拍它,却见它扭头走了。
那次是个例外。之前大多数时候他会待在车里,手握方向盘,把车窗摇下去,嘴里叼着一根烟。他会打开收音机,有时甚至不需要刻意盯着那间房子,因为他很清楚那里住着谁。他还知道后花园有一间马车房,保镖就住在那里。有一次,有辆车穿过车道大门一半时,突然停下了。保镖当时坐在车前面,却轻轻把车子后窗户摇了下来,这样方便车上的人和雷布思进行眼神交流。只见他目光中带着鄙夷、沮丧,甚至怜悯,尽管怜悯是装出来的。
雷布思在想卡弗蒂中年时是否曾对其他任何人产生过类似怜悯的感情。
[1]哈利·阿朗佐·隆格巴,绰号日舞小子(Sundance Kid),美国旧西部时代着名的不法之徒。
[2]这节经文的内容是:“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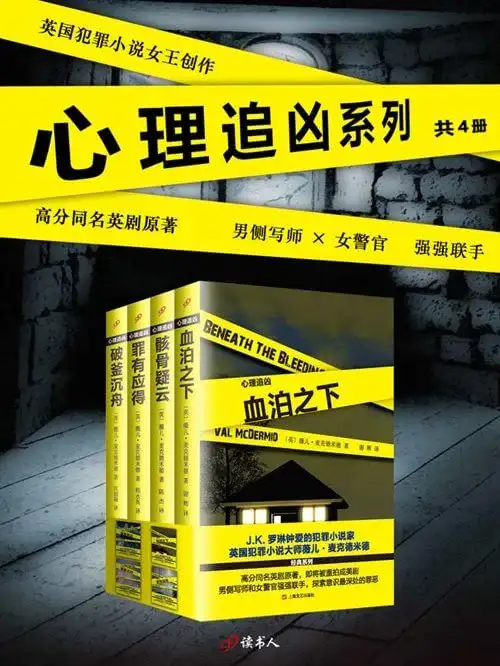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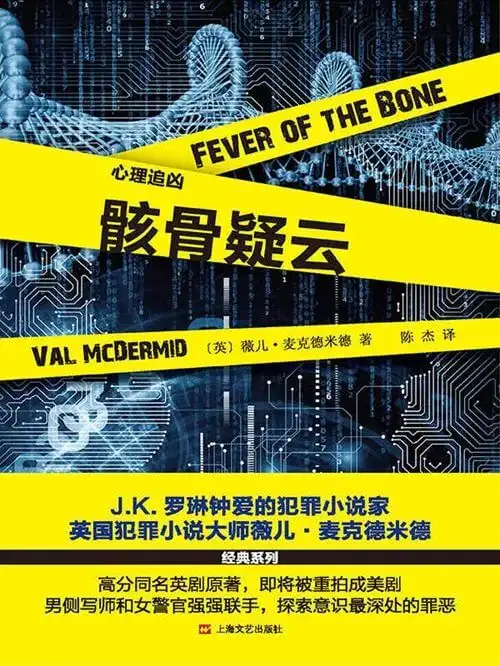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