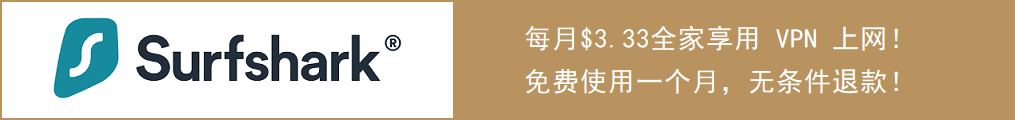
第十三章 和平
6月12号,星期五
纷 争
阳光明媚,有些微热,我们驾车悠闲地逛了七个小时,准备来个天空岛一日游。一路上我们停停走走,去了岛上最大的小镇波特里,参观了岛屿的一家博物馆,还漫步于繁花盛开的唐纳德氏族宫殿和花园。
这些地方说不上无聊,但也不算多有趣,反而是岛上处处弥漫着的宁静祥和,让我们印象深刻。天空岛也被称为“雾岛”,或许是因为小岛大部分时间笼罩在雾霾中,或许是因为在今天这样难得的晴天里,那些海中升起的山脉峭壁,会在水面的薄雾中若隐若现。但如果让我和莉莉给它命名,我们一定会叫它“和平岛”。
对于宁静祥和的事物,我总是格外着迷。
我对于战争的第一次记忆,是自己正穿着睡衣站在楼梯顶层,俯视着我母亲和一群女人坐在客厅里编织。她们自发地聚在一起,为一个名叫“给英国的包裹”的公共计划服务。英国那时在和德国作战,织袜子和毛衣是美国正式参战之前,美国人能为英国提供的支援。在这段记忆中,我在本该已经入睡的时间,偷偷站在楼梯顶上,穿着柔软的法兰绒睡衣,默默注视着这场战争的影响。
此后,美国很快加入了战争,而我则开始了我的“演讲生涯”。每天卧室熄灯后,为了防止被人听见,我都会把自己裹在床单里,弓着身子趴着,幻想着向全世界各国发表演讲——一个八岁孩子的演讲,长篇大论,号召大家维护世界和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那时起,我的心中就有了对于和平的召唤,但我也不排斥为了和平而进行的思想之战,因为它们不涉及真正的暴力或仇恨。这两种存在于我身上的矛盾想法,却并不能作为我人格分裂的证据,因为大多数真理和所有伟大的事情都充满了悖论,和平也是如此。
当然,和平不是自动发生的,它也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和平的实现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精神、天赋、条件、过程、决定等,它是一项长期不懈的任务。而和平的获取,通常需要经过四个阶段:伪共同体阶段,混乱阶段,清空阶段,共同体阶段。
先说说伪共同体。伪共同体是个很恰当的称呼,因为它是一个虚假的共同体。在伪共同体中,一群人会故意表现出和平,假装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或差异,而这种伪饰,是由一套大家都熟知的不成文的规则维持的,即“礼貌”,人们用礼貌掩饰彼此的矛盾。在我看来,这套不成文的规则很无聊,但伪共同体也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维持了群体表面上的和睦,并且在人们之间没有大的问题出现前,使我们能够和睦共处。
但它归根结底是种表面现象,是对真相的伪装和掩饰。当个体间的差异因为某种原因被迫显露出来时,群体即刻就会退化到混乱阶段。在混乱阶段,差异和分歧已经浮出水面,于是,同化尝试就出现了。同化尝试,就是每个人都在试着平复或转化彼此,以此来回归到原先的虚假的统一状态。偶尔地,群体成员会“忍气吞声地接受”他们之间的差异,但是,无论是“平复”还是“转化”,都会让火药味变得越来越浓,直至出现战争或群体自毁局面。虽然,刚刚我用“退化”形容这个阶段,但其实,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进化”。对,就是进化,混乱实际上意味着距离真实更进一步,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也不能避免的一个环节。
如果一个群体里的人都心怀善意(通常是这样的),再加上高水平的领导能力,那么,他们就会从混乱中进化为清空阶段。但这是个艰难的阶段,在清空阶段,群体成员要清空执念,牺牲掉任何阻碍他们成为真正共同体的事情。需要清空的事情举不胜举:死板的日程、偏见、草率给出的回答、对确定性的迫切需要、被他人认可和欣赏的迫切需要、过度的依赖心……这张列表比我们想象得还要长,必须拥有正确的领导方式,清空任务才可能实现。
想做到正确的领导方式,保障清空的完成,需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点,是来自群体的压力,它会让人服从与接受,因此会改善群体行为。第二点,是在利用群体的压力时,并不是简单地让人“为群体牺牲一切”或少数服从多数,没有原则的表面服从是不会起到效果的。正确的领导所倡导的是“清空自身不需要的一切执念”,这样才能听见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当群体成员能很好地完成清空时,共同体便会出现。仿佛忽然之间,整个群体的基调发生了变化,成员们开始更加真实地发言,而且简明扼要。大家还学会了屏息倾听,成员与成员同频共振,同步运转,奏出了和谐的交响乐。即使是复杂的决策,也会因为共同体的出现,而变得事半功倍。
从混乱阶段到清空阶段的演变,通常是时断时续的,但从清空阶段升华为共同体的转变,却是瞬间的,极具戏剧性效果。就好像大门突然就被打开了,一种可以明确感知到的和平气息喷涌而出,接踵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祥和和宁静。
这是令人心醉的体验。
对和平的爱与恨
虽然和平的精神让人陶醉,但我的兴趣其实是和平本身。通常,只有当群体第一次成为共同体时,才能感受到和平精神的存在。此后,它的强度会减弱,但由于此时群体因为已经学会了缔造和平的技能,所以,他们依然能不断维护这个共同体。
在等级森严的组织里,通常是某个个体——比如组织的领导向群体成员下达决定。当一个群体是成员们自己做决策时,便会出现两种决策模式:对立和共识。人们在解决对立时,通常会用投票作为手段,但这种方法的效果并不好,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假共识,投票会引发出人们的输赢心理,让投票人数少的一方心生不满和愤恨,甚至会贬损或破坏投票的决定。而真正的共识则是种双赢决策,能获得所有群体成员发自内心的赞同。做出共识决策也许需要更多时间,但它却是明智的,效果也会更加持久。
只有当群体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在面对重大决定时,得出真正的共识。我曾在我的《不一样的鼓声》中提出,共同体的建设,应该优先于决策。
人们常说,当一个群体凝聚成了共同体,人与人之间会充满“无条件的爱”。这种爱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很多的爱都不是无条件的。事实上,“无条件的爱”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群体成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心与心沟通。
群体最艰难的长期功课,就是一旦共同体形成后,对它的经营维护。群体不会自觉保持共同体状态,在几小时、几天或几周内,共同体将会重新回到混乱或伪共同体状态。一个健康群体的特点就是,它并不总是“在共同体状态下”,当意识到共同体变成散沙时,就会迅速做出反应,并愿意重新恢复共同体。换句话说,共同体的经营维持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重建再重建。
正因为共同体具有以上特性,所以,和平注定是艰巨的课题,任重道远。和平的维护,与和平的实现一样艰难。战争与和平相比起来,战争到来得更加容易,人类经常夜以继日地投身于其中,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愿意对和平进行思考。换句话说,战争能自然而然地来到人类身边,和平却不能。
如果再换个说法,那就是人类通常会抵制和平。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实际上,我曾不止一次从人们对共同体的抵制中,看到了他们对和平的恐惧。人们为何会如此?我逐渐意识到,最大的原因就是人们原始的惰性。建设共同体不是个一劳永逸的对策,但人们通常深信它就是。于是,当刚建立起来的共同体四分五裂时,就会怀疑是整套过程存在问题。我曾有过三次痛心的经历,亲眼看到共同体因人们拒绝重建而前功尽弃。这就好像一群人好不容易得到了宝物,在它展示出其显著成效后,却将它扔掉了。我问过他们为什么不再坚持,他们虽然说法不一,但表达出来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太麻烦了”。
在《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中,我曾指出,懒惰也许就是原罪的本质。这种懒惰不是指不愿意干活或工作,而是思想、情感或精神上的懒惰,我把这作为对人类荒谬性做出的最根本分析。
而今人们相信众生平等,连《独立宣言》中都宣称:“我们坚信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深刻但也最愚蠢的悖论。因为,人类是完全不平等的。
我们有着不同的天赋、倾向和基因,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还有不同的个人经历和能力,等等。事实上,人类应该被称为“不平等的物种”,最让我们区别于其他生灵的,正是我们无与伦比的个体多样性,以及行为的易变性。哪怕仅仅在道德领域,从最恐怖的恶魔到最纯洁的天使之间,我们也可被分为很多个等级,所以,何谓平等?
在“我们是平等的”这一虚假观念的驱使下,人们形成了伪共同体,而当这个假象失败时,人们便企图以征服来实现平等——从婉言说服,到咄咄逼人,征服力度不断升级。我们完全误解了我们的任务,社会的任务不是建立平等,社会的任务是发展制定出好的体制,以此来削弱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体制在合理的情况下,拥护和鼓励多样性与多元化。
人权,是发展这种体制的核心,我全心全意地赞扬《人权法案》,然而,我非常怀疑《独立宣言》所主张的广泛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比如,我现在年事已高,越来越觉得我的生命不属于我,在某些方面,我越来越怀疑我的生命权。作为一位作家和导师,我必须质疑我说谎的自由,甚至是巧妙地歪曲事实的自由。作为一位心理医生和神学家,我深知幸福要么是某种深层追求的副产品,要么是自欺欺人的结果,我不确定追求幸福到底有多大价值。与这些权利相同,和平也是一种权利,但同时,它还是一种义务。
我们不能只想享有和平,却不想尽义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期待和平能毫不费力地自然到来,或期待一旦拥有了和平,就能一劳永逸。权利最大的问题在于,会让人产生视“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心理。那些不断宣称“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可剥夺”的舆论,会让这种心理越来越严重。简而言之,权利有它的好处,有利于个体的发展,但它也是极其危险的陷阱。
关于和平,人们通常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所有的冲突都可以和平解决,这简直太天真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冲突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诉诸武力、暴力或威胁,这种想法可谓损人利己,现实中很多不公正或不必要的战争,纯粹是懒惰和愚蠢的产物,人们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尽管战争被认为是光荣的,但就如同《哈莱克人》所唱的那样,它通常会毁灭人的尊严。所以,我们需要追求的和平,其实是一种不致命的冲突,如果经营得当,不致命的冲突实际上会提升人的尊严。
超越冲突
有可以和平解决的冲突,也有不能和平解决的冲突,除此之外,还有着第三种类型:不能解决,但可以通过“接纳差异”来超越的冲突。这样处理,同样可以实现和平共处,而大到国和国之间,小到婚姻之内,都可以运用这样的处理方式。
我一直记得这样一幕:结婚第一年的一个夏日,我和莉莉站在那间租住的阁楼公寓里,阳光烘烤着屋檐,我们汗流浃背。奇怪的是,我记得这个细节,却全然忘了是什么引发了我们的分歧,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我对莉莉说:“我认为我们之间应该没有秘密。”而她反驳道:“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婚姻中应该有个人秘密,我不打算让你知道。”那次对话后,我们收起了各自的“犄角”,不再针锋相对,彼此攻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依然会亮出自己的犄角。我们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分歧是真实存在的。刚开始,我认为莉莉看重秘密是错误的,我有责任帮她打开心结,而莉莉则希望我能快点儿成熟起来,不再是个口无遮拦的大嘴巴。渐渐地,虽然我们并没有放弃各自的倾向,但也看到了对方立场的合理性,事实上,如果现在让我们代表对方去进行一场强有力的辩论,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莉莉早已欣赏我的直言不讳,并能在大多数时候将之视为我的天赋,而我也能理解她对私密性的需要,视她的慎言为天赋。分歧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慢慢认识到,接纳并欣赏彼此的差异,要比消除差异更重要。因此,通过超越分歧,我们实现了和平。
想要超越分歧,需要不断修正自己的立场,直至它们不再是立场。
年长带来的“特权”之一,就是学会了如何真实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些年来,我和莉莉越来越懂得行使这个权利,与此同时,我们也学到了如何保持沉默,或表达得含蓄。
关于秘密的看法,并不是我和莉莉唯一的不同。之前,我谈到过我和莉莉不同的购物方式,我曾打趣说,这是因为男人为了直接购物,女人则是为了逛街放松。而近年来,我发现通过“社会生物学”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这一理论认为,我们的社会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早在旧石器时代,男人是狩猎高手,女人则负责采集那些可以食用的植物,他们都有着明确的生存价值。因此,人类的“适者生存”最终演变成了:现代男人成了猎人,而现代女人则是采集者。
虽然有些人对这个理论嗤之以鼻,然而,根据我和莉莉的购物习惯,我认为它颇有可取之处。莉莉的确天生就是个采集者,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天生是个猎人,然而,当我全神贯注地对一个想法穷追不舍时,莉莉也会觉得我像是在追踪猎物。
打高尔夫球时,我关心的是击球进洞,但每次在灌木丛下大海捞针一样地找球时,我一点儿耐心都没有。莉莉则不同,一旦她打出一两次臭球后,就不会一门心思偏要把球送进洞里了。于是,我们在打球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我一杆一杆地击球,不将球击进那个洞誓不罢休,她则在灌木丛里兴高采烈地捡拾我遗失的球,甚至还能捡到很多别人的球。当我俩搭档一起打球时,凭着莉莉出色的搜集工作,我们回家时带的球,至少会是带来的两倍。
性别差异通常会造成分歧,以至于它们引发的冲突一直被称为“两性之战”。虽然我和莉莉也会不由自主卷入这种战争中,但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做到超越这种战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分歧就此解决了,比如,虽然我接受了莉莉对化妆品和发型师的需要,但我对她的这种行为没有共情;虽然有时我会用猎人的眼光看其他女性,对我的这种倾向,她也不会产生共情。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做不到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事情。
当我们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事情时,共情由此产生,冲突也就找到了解决之道。举个例子来说,我一直不习惯英国人的左行制,所以总是将车开出路左边,这让莉莉认为我笨手笨脚,心不在焉。在过去的12天里,每当我蹭到了左边的路牙时,莉莉就会对我尖叫。而今天在天空岛,因为我的背又难受起来,所以她来开车,当她不断地像我一样将车开上路牙时,她的同理心一下增加了。
啊哈,理解万岁,和平万岁。
刚刚我谈论了很多与和平有关的话题,但说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除此以外,一个人内在也存在着和平问题,那就是人们渴望得到的“内心的宁静”。
我常告诉我的患者,心理治疗和快乐无关,而是和力量有关。如果一个人能提升自身的能量,即使自己无法因此变得更快乐,但一定能因此变得更有能力。生活中存在很多能力的真空地带,需要有能力的人去开发,所以,一旦一个人变得更有能力,也就因此更有了责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一个人不再只为自己考量时,将会带给自己一种快乐或内心的宁静,因为你知晓自己肩负重任,而不再会被小我的琐事压垮。
我们倡导缔造共同体,但实际上,自己和自己也能达成一个共同体。当我们懂得自己,和自身所有不同的一切保持关系,包括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善和恶、光明面和阴暗面时,我们也就实现了和自己的共处,由此,使身体和心灵成为一体。我之前提到过,卡尔·荣格将“拒绝面对阴影”视为人类的邪恶根源,阴影就是自身不愿意具备的那些特质,它们被我们不停地扫进意识的地毯之下藏起来。而荣格认为,由于我们拒绝面对自身的阴影,我们就是在从根本上避免和真实的自己联系。
我们每个人都有阴影面,群体也不例外。相对于伪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处理其自身阴影的群体”。历史上战争的发动者,往往是些自我不完整的个人或群体,他们为了不受良心的谴责,会急迫地和自身的恶切割,他们会为自身的优点感到骄傲,但缺乏谦卑之心,无法看见自身的弱点和盲点,更不能认真去处理自身的阴影。
三年前,在一次关于共同体的大会上,一位发言者说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话:“你无法隔着距离建立共同体。”这句话真的太深刻了!假设富人总是待在由保安把守的豪宅里,是不可能和贫困的人结成共同体的;如果老师总是高高在上,就无法和自己的学生成为共同体。就像共同体有真伪之分一样,内心的宁静也有真与假的区别。假的内心宁静,源自和真实自我的脱节,而真正的内心宁静,则要求我们熟知自身的任何一面,并和它们近距离接触。
青铜之后
我所思考的这一切,似乎和石头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今天连一块石头都没见到——但事实上,却关系紧密。
我和莉莉之所以对石头如此着迷,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神秘,而关于缔造出这些神秘的巨石人,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凯尔特人约公元前500年抵达不列颠时,他们捣鼓了一阵子巨石,但却没有竖起巨石,巨石文化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消失。为什么?巨石文化为何会失去它非凡的生命力?
莉莉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提示。就在她今天一边开车,一边时不时撞上路牙时,她说出了一番大胆的假设:“你知道的,我喜欢小精灵和小仙子,它们和爱尔兰传说中的小妖精很像,都被统称为‘小矮人’或‘小人儿’。而且,它们有个共同之处,它们都讨厌铁。我在想,也许它们不是讨厌铁,而是害怕铁。你说过,是凯尔特人将铁带到了不列颠,所以,那些小矮人会不会是前凯尔特人或巨石人?”
这听着实在天马行空,但并非全无逻辑。只不过,根据考古学家出土的巨石人遗骨表明,他们并不比今天的我们矮太多,甚至差不多和凯尔特人一样高。而且,远在凯尔特人带着铁来的1000多年前,巨石文化就已经开始衰落了,这种衰落很可能更多的和青铜的出现有关。
在大不列颠的青铜器时代,人们确实建立了几个石圈和石林,但数量极少,而且他们用的石头大多又矮又小,只有60到120厘米高,就好像他们只是在敷衍地走个过场,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惊人的集体力量或对祖先的虔诚。
但还有其他非常显著的变化。比如考古学家相信,大不列颠某些地区在青铜器时代划分出了土地拥有权,证据就是那些被建立起的石墙。
至于巨石人没落的最主要理由,则是他们从群居文化过渡到了一种和我们现今相似的文化:一个具有明显社会阶层的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权、战争和盗窃。这场过渡,似乎和青铜的引进密切相关,这种引进是革命性的,它诱发了货币和财富竞争的出现。
小精灵和小仙子或许能做到与自然和彼此和谐共处,但我却并不知道巨石人是否能实现和平共处,然而,我们确实看到了,他们在大不列颠和欧洲西北部集体建造了意义非凡的纪念碑。之后,随着青铜的出现,他们不知为何失去了集体的伟大力量。这似乎隐隐印证了,传说中的那些小矮人们为何害怕金属。
这一天的傍晚,我和莉莉来到了一家干净的小饭馆吃晚餐,女服务生十分热情得体,在得知我们将在次日清晨前往刘易斯和哈里斯岛时,她兴奋地介绍道:“你们到那儿时,一定得去看看卡拉尼什巨石圈,它们简直棒极了!”她大声说着,压根不知道我们是石头迷。
我和莉莉一下子振作了起来。晚饭后,我们沿着海湾散步,虽然现在我还不能预测英国的天气,但我们注意到,今晚西边方向的天空积起了高云,毫无疑问,一场特大风暴即将来临,而且时间很可能会是我们明天乘船途中。
回到宾馆,带着对明天的期待,和一丝惴惴不安,我们很快入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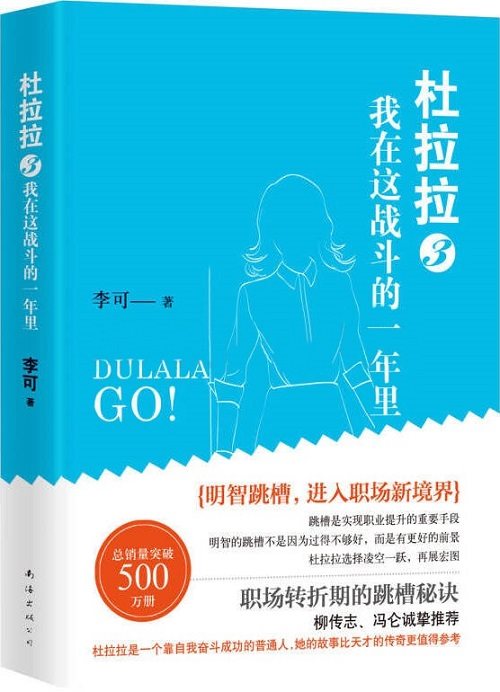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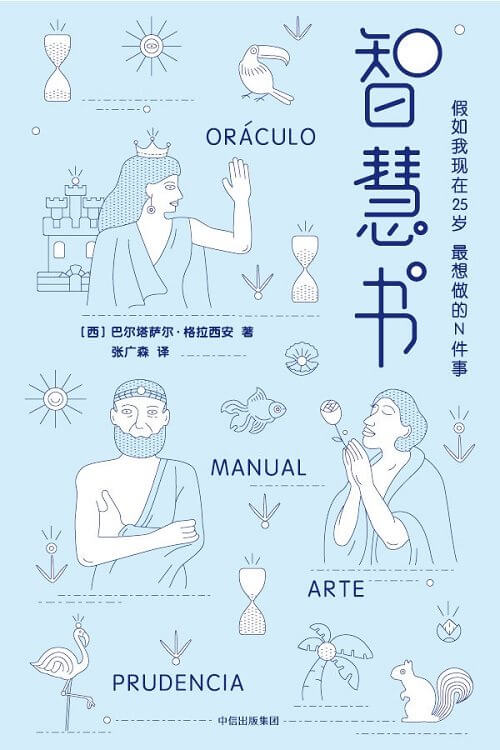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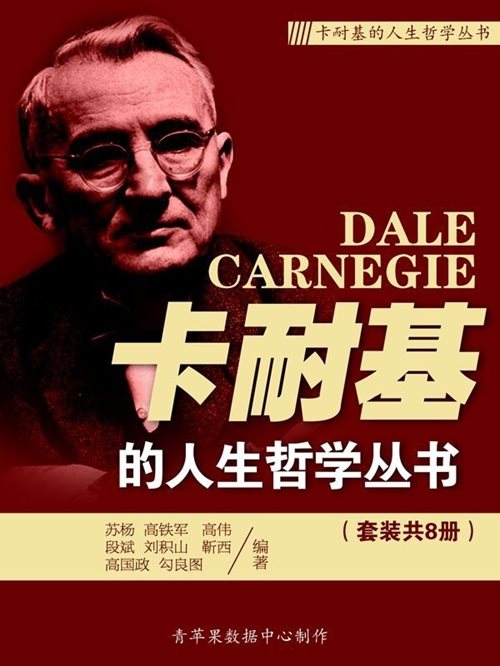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