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死亡
6月9号,星期二
至 美
我们一早就离开了格拉斯哥,冒着瓢泼大雨,前往罗梦湖西岸。
罗梦湖!童年时的记忆像雨雾一样席卷了我的全身。我在英国文法学校上学时,唱的歌并不全都是《哈莱克人》那样的战斗歌曲,还有一些是温柔凄美的情歌,有一首歌,我每次唱起都会分外激动:
噢,你将踏上山路,
我将走在平原,
我会比你先到苏格兰;
但我和我的真爱再也不会
在美丽的,美丽的罗梦湖畔相见
差不多50年后,一同和我走在这条路上的,是莉莉。除了神,她是我的最爱,而且我们正处于我曾深情歌唱过的罗梦湖畔。
雨流如注,一阵阵的雾气飘荡回旋着,虽然下雨影响了视线,但我们知道这里美不胜收。这是种无法描述的美,即使一个人从没见过,也应该相信这世上有这么一种美,哪怕在雾气中我们看不清山顶或湖岸,但我们真的感觉自己来到了地球上最美的地方。
因为大雨的关系,我们没有在美丽的罗梦湖畔多做停留,而是继续前行,驶入基尔马廷山谷。这里的风景虽然没有那么惊艳,但胜在柔美幽静,令人心旷神怡。而我们之所以匆匆告别罗梦湖畔,也不全是天气使然,因为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基尔马廷山谷曾是巨石文明的中心之一。才一日无石,我们对它的思念就已如饥似渴。
基尔马廷山谷不仅因为石头出名,还有一座足够神秘的建筑——杜纳德城堡,它曾是达尔里阿达王国的中心要塞。达尔里阿达是大约公元500年时一个苏格兰部落,杜纳德城堡也是这个部落在随后500年里国王加冕的地方。当我和莉莉置身其中时,确实感受到了一种悠久的古老气息,它带着我们穿越至1000年前,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群身披毛皮的武士聚在这里,以生命宣誓效忠。如果让我在威斯敏特大教堂和杜纳德城堡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也会选择后者作为加冕的地点。
然而,这座城堡最让人们熟知的,却是野猪。在城堡顶部的巨石间,卧着两块大石头,大一些的那块上面刻有一个深深的脚印,以及一只浅浅的野猪图案。虽然刻画得很浅,但手法精湛,野猪看起来栩栩如生,让人惊叹不已。而在旁边那块小一些的石头上,则刻着一个简单的圆形图案,或许叫“杯形”也可以。此刻我和莉莉意识到,野猪石刻是史后的,而这个简单的杯形,则是巨石人的典型标志,那么,它很可能是出现于史前。
杜纳德城堡位置优越,气度非凡,它高高在上,俯瞰着山谷里的激荡河流,简直是个天然的神圣之地,不仅适合国王加冕,也适合举行任何庄严的仪式。我猜测,这里曾经也是史前巨石文化的圣地,后来被达尔里阿达人据为己有,在基尔马廷山谷留下了了不起的标记。
在花了一个小时探索城堡后,我和莉莉告别了这座让人回味的城堡,继续上路,准备前去研究巨石古迹。
我们想要找的,是一种叫阿赫纳布瑞克石刻的遗迹。按照地图的指示,我们将车停在一条土路的尽头,然后踏着美丽的苔藓小径,穿过一片迷宫似的橡树林,然后再经过一座农庄,一块草甸,爬上山顶的松树林后,终于发现了我们寻找的东西。它位于松树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上,几块裸露的岩石上面,大量地刻着几乎同样大小的同心圆图案,这些图案被简称为“圆环”。
有些圆环直径约30厘米,内有三个同心圆。其他的直径约1米,内刻最多有7个同心圆。有的圆环重叠,看起来宛如层层涟漪。很多圆环在终点没有合拢,更像是旋涡,而不是完整的环形。我们立刻就认出来,我们在英格兰朗·梅格古石上看见的那两个图形,和这些属于同一种艺术。事实上,除了原始的空心或“杯形”以及石头本身,圆环是不列颠群岛巨石文化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艺术形式。
见多识广的现代人也许会认为,这些同心圆的集合称不上“艺术”。
然而,这些圆环在用线条诉说着它们的古老,其本身就是一种难言的魅力,让人觉得兴奋好奇。
死亡的地位
基尔马廷山谷有许多天然岩画古迹,但时间有限,我们没能一一参观。站在山顶,我们能看到,谷中四处是形形色色的石林或竖石碑。它们有两种排列模式,一种是一组六块石头紧密匀称地排列成行,还有一种就是五块石头间距很大地站立着,一字排开,且呈直线分别排列在三块田地的地头。
而大多数的竖石碑,仅是简简单单的一块石头,形单影只,独成风景。我和莉莉亲手抚摸了一块竖石碑,它在一块墓地的后墙处,身披青苔,掩映在金雀花丛中。我们又根据地图找到了另一块,但它藏在一栋农屋后院里的晾衣绳下面,之所以用“藏”,是因为这块石头很不起眼,还不到一米高,当晾衣绳的柱子都不够,以至于当我终于辨认出它之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不过,山谷下面倒有块竖石碑和朗·梅格一样高挑,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接近它。好在还有些石头虽然不是很高大,但同样古老沧桑,并且它们就靠近路边,我和莉莉特意拥抱了其中的好几块。
基尔马廷山谷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里遍布山谷的石墓。
最密集的当属一排长达3公里的石墓。它们被集体称为拉吉石堆古迹,构成了一座有着4000年历史的古代大墓地。
巨石人对死亡的重视显而易见,他们用三种独特的方式,凸显了死亡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第一种,是对巨石的使用。他们大量开采并使用巨石,其中就包括建造坟墓。石头不会腐烂,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告诉了我们,古人为何会这样做。
第二种,他们不会特别关注单个的死者。在这些巨石墓室里,常常不止一副尸骨残骸,而是很多。看来,和其他文化一样,巨石人偏爱群体安葬。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他们不辞辛劳、兴师动众建起巨石坟墓的原因——这类坟墓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旦建成也不需要再维护。
仅仅是这两点,也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我和莉莉之前见过类似的习俗。我们在冲绳岛度过了三年美好时光,当地居民有种古老传统,会用巨大的水泥制作的子宫形陵墓,安放逝去亲人的遗骨,一座陵墓中往往埋葬着好几代人,有些陵墓甚至排列到了高尔夫球场的球道上。
巨石人的石墓第三点独特之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巨石公墓的种类实在繁多。它们有些建于地下,有些建在地面上。许多是圆形丘墓,上面覆盖着普通石块;有的延伸有好几米长,形成了长而窄的古坟堆;有的干脆什么也没有覆盖,只遗留下来某种支石墓或石圈,突兀地伸向天空。有些墓冢只有一个墓室;有的有好几个。
此外,考古发现出的尸骨残骸也展示出迥然各异的故事。有些残骸自然腐烂后才被埋葬起来;有些则是人去世后直接入土为安;有的明显经过了焚烧。而且,这些尸骨的完整性也是各种各样,有的缺少手和脚,有的没有头骨,有的整副尸骨都是分开的,头骨在一座坟墓中,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出现在另一座坟墓中。总之,形式之多样难以尽述,似乎巨石人在拿死者做着某种实验。
拉吉石堆古迹大墓地非常大,我们只参观了一小部分,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坦布尔伍德石圈。它是一座石堆墓,看起来非常整齐干净。在石堆的中心,是个小长方形的墓状凸起。而最显眼的,则是一些
1.2米高的巨石,它们从岩石块中脱颖而出,站立成圈。其中一块巨石上清晰地刻着两个终端未合拢的圆环或螺旋形。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个石圈是由公元前3000年的早期巨石人竖立起来的,直到1000年后,后来的巨石人开始朝这里扔石块,因而才形成了石堆墓。
我真希望他们没这样做。对我来说,石圈本身就很独特美丽了,如果它们能单独矗立在那里最好不过。我喜欢看见巨石们未被打扰的纯粹美,而外面那堆包围着的石块,无论被摆放得多么整齐,也不过是画蛇添足。
安 葬
自古以来,人们都试图通过某种丧葬仪式,来确保自己不朽或永生。通常,人们肉身还未死,就已经安排好了身后事宜,埃及法老们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即便是今日,也有些人选择在死亡那一刻将自己的身体冰冻起来,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某些人能用些手段使其复活。
我很难赞同这类行为,在我看来,这十分愚蠢。人们在生死问题上总是矛盾的,既相信灵魂永恒,又明显地贪生,希望肉身不死。即使有一天人真的能做到肉身不死,我也不想这样,对我而言,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扛起自己的尸体继续苟活,实在是件低级无趣的事。
我渴望灵魂能从肉身中解脱出来,但也明白身体的各种好处。如果没有身体,一切也就都无从谈起,但我信仰的“道成肉身”,即无形的道与具体肉身的统一,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的内心,必须通过肉身的实践来实现。就像我们的FCE,再美好的愿景,如果没有员工、志愿者这些活生生的人将其转化为行动,那么也就毫无价值。
尽管如此,我依然不崇拜肉体。我的内分泌腺体曾驱使我在性上做出轻率之事,我患流感时感觉如同噩梦,四十年的背疼带给我无穷无尽的折磨,但每当我想起自己的时候,想到的并不是这具肉身。就如同我看待莉莉,也不会将其仅仅视为一具肉体,而是会想到她不羁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决定了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的躯壳。因此,说起死亡,我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无须拖着这具躯壳四处奔波,不再受制于身体,而是能够超越时空,自由旅行。
而防止肉身腐烂或竖立墓穴纪念碑,也是自大傲慢的体现。除了希望征服死亡,没有什么动机能让人干出这样的蠢事。虽然我嗜烟如命,但我绝对不会自负地认为自己可以打败死亡,绝对不患肺癌。即使是那些神圣故事中的复活情节,其意义也不是为了证明我们能战胜死亡,而是想告诉人们,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就如同花儿谢了,它把生命留在了种子里,音乐家去了,他把生命留在了音乐中,我们的存在并非只有肉体这一种形式。
话虽如此,但墓葬存在的更重要作用,并不是为了迎合死去之人的渴望,而是为了满足在世之人的欲望。逝去的巨石人无法搬来那些石头,溘然长逝的现代人也没有给殡仪工作者写支票,是活下来的人在做这一切。为什么人们要如此?原因同样多种多样。
我怀疑,这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对死亡的多重否定。我们觉得即使只留下自己的几根骨头,也算是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也许灵魂已散,但那些遗骨证明死亡并没有让人彻底消失,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我虽然对这件事毫不欣慰,但很多人却很在乎,会认为逝者的在天之灵如果看到我们对他的遗骸足够尊重,就会对我们友善,不会来捉我们去地狱,甚至会庇护我们长寿,这是一种宛如投桃报李的交换。
还有很多人认为,如果我们尊重父母的遗体,我们的孩子也会尊重我们的。
还有一点就是,安葬亲人给了我们一些可做之事,以应对死亡造成的束手无策。最现代的医学,也无法让死亡销声匿迹。而我们只要继续去逝者的坟前扫墓祭祀,也许能从这种无助感中得到些许安慰,这对我们来说是种心灵寄托。在死亡面前,至少在表面上,我们依然保有一些控制权。
虽然,我能从精神分析角度上理解这些心理,但作为理性时代的产物,我还会觉得以上这些心理动机是种病态。或许我本就是个没有同理心的人吧。
随着我和莉莉的年龄增长,莉莉的胆固醇水平越来越高,我的肺病变得严重,哮鸣音越来越厉害,我们愈发想知道,两个人中谁会先走。
当然,作为理性时代的产物,当这一天来临时,不论我俩谁先走,我们不会哀痛欲绝,也不会举办兴师动众的仪式。如果莉莉先我而去,我敢确定,我希望她的骨灰装在漂亮的小盒子里,葬于优美之地,并标以记号,好让我以后能找到她。我想象着,在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来她在的地方坐一会儿,对她说:“嘿,亲爱的,是我啊。你好吗?我很想你,我一切还算过得去。我给你说说这段日子里的事……”
仅此而已。
不要墓碑。不要灵柩存遗骨。不要为莉莉做,也不要为我做。我不想受身体的束缚,更不想受仪式的束缚,我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大约30年前,我写了一首诗,叫“生命的愿望”,表达了我对解放躯壳的向往:
当我死后,
我将不再
属于你们。
勿葬我
于你们之间,
但携我
去空旷之地;
且为我
去除皮带和搭扣,
留下我
赤身裸体在那儿。
温柔的昆虫
会在我的发间玩耍,
野兽和大黑鸟
将发现我的血肉冰凉,
那已是下昼。
而至入夜,
我枯萎的眼睛
会平静地反射出
遥远的星子
散发的光,
那时我会
感谢你。
死亡渴望
我并非冷血,我也会悲伤,只不过我不会像多数人那样去表达悲伤。通常,人们在离别后才感到悲伤,而我的离愁别绪,则发生在离别之前。
我初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我和莉莉离开冲绳岛的四个月前。某天下午,我坐在山顶上,意识到我已经在这个岛上待了三年,并且要和它说再见了。当我们真的动身离开的时候,我没有恋恋不舍,至少在意识层面上我没感觉到,但是每年中总有一两次,我会梦到我还在那里,或是回到那了。
我和莉莉还会想到彼此的死亡。早些年,我们的婚姻比较坎坷的时候,想法通常是这样的:“如果她得了白血病,当然,我希望她不会。
但如果她得了呢?我会一直守在她身边直至最后一刻。然后我该做什么?我会立刻开始和人约会吗?约谁?嗯,让我们先看看……”但现在,我们想到彼此的死亡,不会再幻想自己因此能得到自由,而是在做心理的准备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哀悼,正在准备我们的告别。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苟延残喘地死去,是件痛苦的事。我们的父母都在去世之前,经历了缓慢的衰竭过程,这对他们来说是种折磨。这也意味着,在他们每个人撒手人寰之前,我已在离愁中生活了五年,因此,那一天最终来临时,我真心将此视为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的悲伤很清浅。我本来准备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为她举行仪式,协助我的是我的导师玛拉奇。一天,他打电话问我情况如何。“我一切都很好,玛拉奇,”我对他说,“只不过我母亲上个星期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他大声说。
“我倒没有。”我明确地对他说,“她遭了很大的罪,病了那么久,我很高兴她终于结束了。我唯一难过的是,她走的时候我不在她身边,临终之际,就她一个人。”
我对墓葬从来不感兴趣,事实上,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对死亡都怀有浪漫的思想,尤其是我自己的死亡。我父母常告诫我很多事尽量不要去想,死亡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自己也尽可能地避免思考死亡。然而,对我来说,它曾是、现在依然也是,一个非常让人着迷的冥想主题。当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我认为,死亡也许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实——天地有万古,此身不再得,至少生理上如此。我对死亡的浪漫想法,让我更深地体会到我们短暂存在的意义。
我对死亡没有排斥心理,让我比大多数人少了牵挂,从而心灵更加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死亡不恐惧。理智上我认为,死亡这一真实存在的未来,在很多方面让人欣慰,但在情感上,我发现死亡是可怕的。我对死亡感到害怕有两个原因。
其中稍微次要的原因,和我的写作有关。除了写作,我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可有可无的。我的孩子们不再需要我了。莉莉是个坚强的人,没有我她也一样过得好。我留下的遗产足以让孩子们生活富足。幸运的是,FCE在经济和管理上都已独立。而且,我的大部分演讲已经做过了录音或编辑。但是,唯独当我写一本书的时候,我会无比珍重自己。我害怕我会在还未完稿之前就撒手人寰,我的书需要我。除了我自己,没人能写出我要写的东西。我在意的,不是可能会损失一笔收入,或心疼投入的时间和心血,而是怕我酝酿的那些想法胎死腹中,永不见天日,这才让我害怕。而这种惶恐与焦虑,是很多作家的通病。
我害怕死亡的主要原因,则是“我”的死亡。我是个相信前世今生的人,但相信这件事和确定这件事,是两码事,在我内心深处,我最恐惧的事就是“我”不存在了。你可以说这是自恋、依附心理、生存本能或任何你认为的可能性,明显的事实就是,我害怕死。我害怕的不是肉体的灰飞烟灭,而是我将不复存在,世上再无斯科特·派克了,就跟他从来不曾存在一样。我很害怕当我辞世时,面对的是寂灭深渊。
九年前,我同时感染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细菌性肺炎。而在我住院的第二天下午,我忽然惊慌失措地对莉莉说:“我无法呼吸了。”她跑出去叫来了护士。护士看见我的脸都紫了,立刻安排了呼吸机,我一下得到了缓解。但即便得到了精心护理,我的脸还是过了好几天以后才不发紫,可怜的莉莉守在我旁边寸步不离。我曾站在死亡深渊的悬崖边,我不想再体验那种感觉了,虽然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弗洛伊德学说主张,我们有生存渴望和死亡渴望。对我而言,这并不是理论,而是现实。死亡渴望在我身上显而易见,我宁愿继续吸着心爱的香烟自毁,也不想痛苦地多活一两年。而今我已经将近60岁,我开始觉得疲惫,但还没累到想要放弃生命,但如果让我这么活上三四百年,我认为还是早点儿死的好。而在未来几十年,我的身体和精神将会变得更疲惫不堪,这种对于生的疲惫,会逐渐克服对于死的恐惧。遗憾的是,它并不会消除我的恐惧,仅仅能克服它而已。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的生存渴望依然明显。虽然我不喜欢为了锻炼而锻炼(准确地说,是一直讨厌),但现在每天清晨,我依然会喝杯咖啡,吸一两根烟,再做几分钟祷告,以鼓励自己硬着头皮进行15分钟愚蠢的背部练习。如果我不做的话,我的脊椎将会在几个星期内僵死,然后我很快就会死掉。无论如何,我还有些事想做,还有些地方想去看看。我依然热爱着生活,但我说不准我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做背部运动时,到底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还是对死亡的恐惧。
落 幕
我确实有不少想要做的事和想要看的地方,比如今天下午就是如此。我们离开基尔马廷山谷的时候,雨停了,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到了今天的终点站奥本。而此刻虽然已近傍晚,但太阳依然明亮耀眼。
奥本和格拉斯哥有着天壤之别,这里是个理想的落脚点。它坐落在苏格兰大陆西海岸的一个美丽海湾上,气质介于小镇和城市之间,建筑多为维多利亚风格。我们下榻的科伦巴酒店,是其中最具维多利亚特色的建筑,它奇异别致,是栋高而窄的六层楼,立在海湾中间一块小小的凸起之处,就像个竖起来的巨型火柴盒。我们的客房很小,并且有扇宽大沉重的窗户,我和莉莉好不容易打开了窗,立刻,强烈的、略带咸味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令人感到愉悦。
从窗户望出去,正好能看到奥本引人注目的南码头。很多人在悠闲地散步,有种假日的气氛,潮水已退,海鸥鸣叫,此起彼伏,色彩鲜艳的小渔船搁浅在沙滩上,斜斜地躺着,别有一番趣味。就在我和莉莉开始吃晚餐时,海鸥成群结队地涌向窗台。没有它们不喜欢吃的,甚至连斯提尔顿奶酪也不放过。我们还有很多在格拉斯哥剩下的面包,它们欢快地拍着翅膀,争先恐后地在窗台上抢食这意外美味。我们和这些海鸥一起吃完了饭,很快,远处传来了风笛声。我和莉莉聆听着,猜想它来自哪里,而这奔放的乐声突然四处响起,大约十分钟后,身着橙色裙子的风笛手们陆续出现在街道上,四个人一排地组成了四排,向着码头走去,看来要有场音乐会了!
虽然已经是老胳膊老腿,我和莉莉还是雀跃着下了楼。音乐会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风笛手们——当然都是男性,他们气度非凡,英俊帅气,肺活量也是一流的。他们表演了独奏、二重奏和合奏,奏遍了风笛乐的所有形式。他们兴高采烈地吹奏着,技艺精湛,劲头十足。当他们最后伸出帽子的时候,我和莉莉把我们身上所有的硬币搜刮到一起,都给了他们,大约超过了5英镑,但我们觉得物超所值。
之后,我们沐浴着夕阳,沿着码头散步回科伦巴。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在美妙的风笛声中,落下了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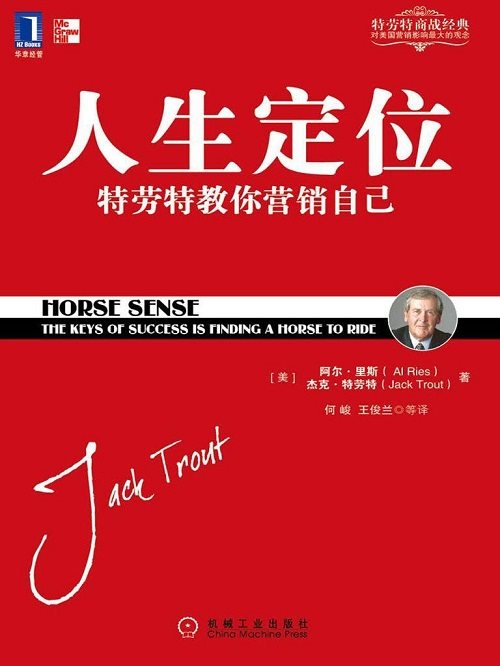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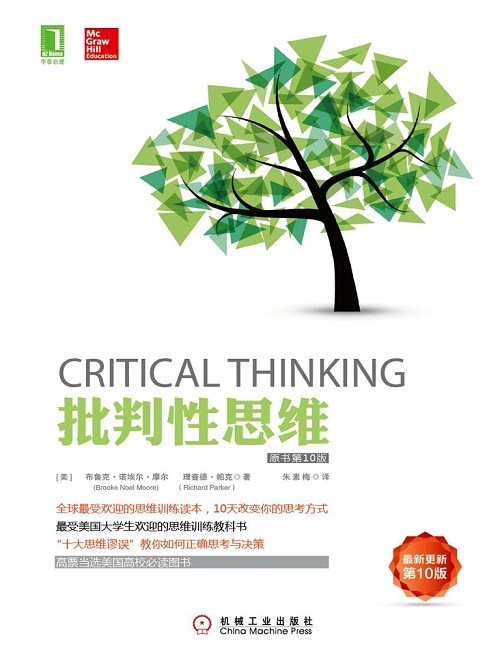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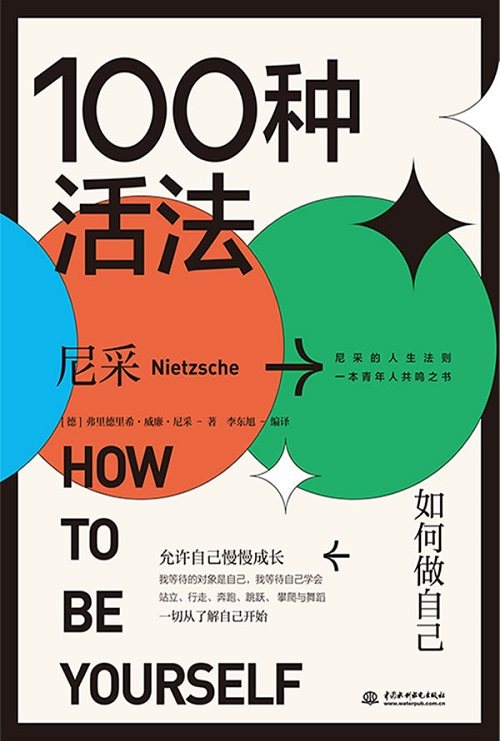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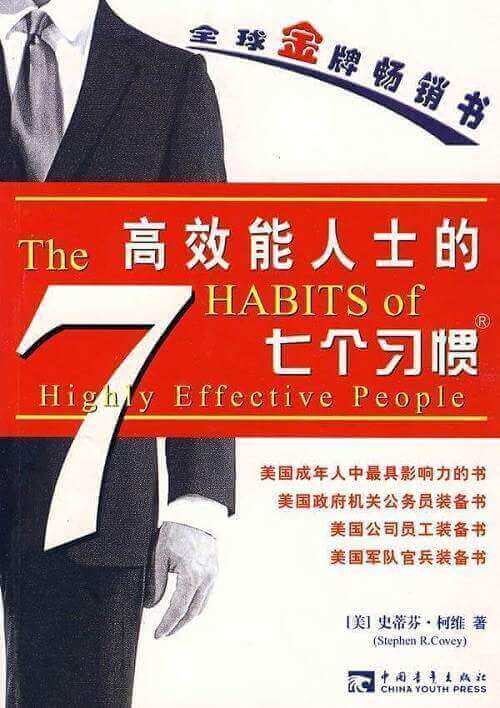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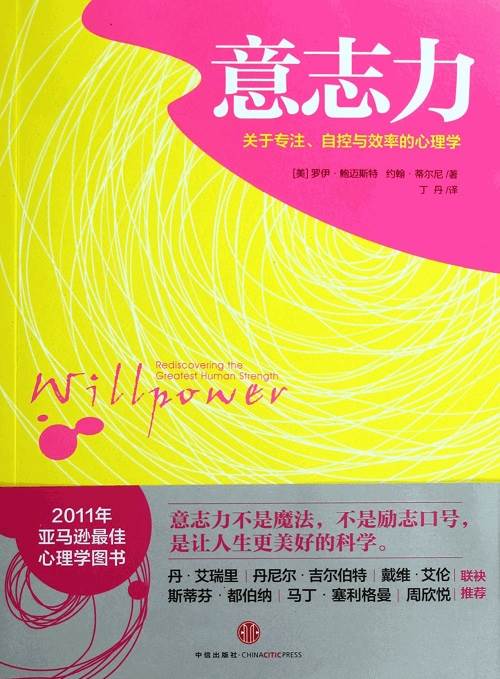
本书评论